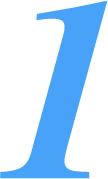早年命運中的三次機緣(連載·五)
時間:2021-04-14 歷史與文化

算無遺策 容後補敘
我畢竟在斯坦福高端智庫工作了34年,平日關注了相關文章,又同智庫主任保持了密切的合作,所以對智庫的運作稍有了解。我在下面談一下情況,並結合中外智庫建設的長短項,以饗讀者。
美國知名智庫游刃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間,對媒體、公眾輿論及政府決策擁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在美國政府某項重大政策出台前,各類智庫在不同程度上廣泛參與了政策擬定的過程。在美國政府決策過程中,往往是在研究和討論的基礎上,由各類智庫率先提出建議,經過上上下下的反復研究商討,然後經由媒體討論、民意測試和國會聽證等程序,最後被政府採納施行。
在美國國家戰略方針的決策過程中,美國政府調研部門和民間智庫是相輔相成的。在建言獻策層面上,兩者在決策過程中的各自功能存在一定差別。總體來說,政府調研部門所起的作用是直接的,但僅在短期內奏效;而各類智庫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卻往往在長期內有效。
在學術界,一般說來,短線課題指的是政策建言,長線課題指的是學術論文。就效應的顯微和長短來說,短線課題作用直接而顯著,效應期卻不長;長線課題作用間接而微小,然而,假如長線課題確實包含真知灼見,縱使一時沒有引起共鳴,最終說來,效應期卻遠為持久。
無論國內外,容易奏效而激起共鳴,從而引起高層注意的,大多數屬於短線課題。換言之,上級領導重視的主要是短線課題。當然,短線課題的成果要一鳴驚人,先決條件是課題主持人必須具有悟性,還要具備足夠的學養和定力。況且,短線課題容易獲得上級領導重視,並可拿到不菲的課題費,是智庫的財源,尤其是在智庫創辦的初期,需要獲得智庫主持人的特別關照。
從美國智庫發展的狀況來看,如果缺乏長線課題的支撐,單憑短線課題單打獨鬥,畢竟缺乏後勁,不能持久。如果一個智庫在處理長短線課題時,能做到長短線有效配合,則智庫賴以生存的財源才能做到生生不絕、化化無窮。
按照斯坦福大學智庫的經驗,往往由知名學者承擔短線課題,由相關學院的師資力量承擔長線課題。在學院執教的教授們籌集資金能力有限,但他們耐得住寂寞,畢竟做學問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才可能做到實至名歸。因此,由他們承擔長線課題較為合宜。
總之,高校學院、智庫需要揚長避短,發揮各自的強項,做到長短線有效配合。這樣,智庫就能做到集中智力,在攻堅時謀求重點突破,進而在將來做到綜合平衡,有序發展。
當前眾多國人縱論天下事,競相趕時髦,凡事均歸咎於體制。彼輩對外怨恨,傾向於罵外邦“白眼狼”;對內不滿,則動輒指出“這是體制問題”。於是乎,外部矛盾一概歸咎於外邦;內部問題則推諉為“體制問題”。究其實質,無非遇事從不建言獻策,卻動輒怨天尤人。如此作風,究竟於事何補?
開國上將張愛萍在與他兒子張勝兩代軍人的對話中,直言指出:“說什麼問題全出在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乾乾淨淨!”這就畫龍點睛地點出了體制弊端與是否善於從建言獻策中汲取精華之間的辯證關係。
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有一句名言:“Do the right thing”遠比“do thing right”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戰略規劃而言,做對的事,要比把事情做對重要得多。高層是要規劃如何做對的事,而基層則是要思量如何去把事情做對。
頂層設計,亦即戰略規劃。戰略規劃正確的話,縱使政治體制一時不動大手術,也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大踏步地前進。如果戰略規劃乖誤,則適得其反矣,越是堅決貫徹,惡果越是嚴重。假若此時再在體制上動大手術,勢必土崩魚爛矣。
至此,再回歸正題,劉易斯與我究竟是如何平衡撰寫學術專著及大戰略研判這兩件事的。對於我在研判中國戰略武器研製工程上的判斷,劉易斯相信無疑,因為我都持有書面資料直接或間接地證明我的判斷,我會一一翻譯或記敘。我在圖書館翻檢資料、去偽存真、分析判斷乃至獲得結論,都由自己決定。待我寫成一章的初稿時,再交給他,彼此商榷定稿。
至於大戰略研判,我可以坦陳,在智庫工作34年期間,凡是劉易斯問及某些國際熱點問題的未來走向,我把自己的判斷告訴他,基本上每次都體現出預見性。其實,始自我對國際政治感到興趣之日,我的判斷可以稱為算無遺策。
起初劉易斯不相信我們能對國際熱點問題的未來走向作出準確的判斷。那時他說,你僅憑幾份報刊,就能進行大戰略研究啦?你倒試試給我看。
其後,我試了幾次,一段時期以後,看來我的預測倒也不失準頭。劉易斯覺得蹊蹺,就對我說,“You just made a good shot (你不過是猜中罷了)”。對此,他始終將信將疑,不予採信。直到很晚,在2016年,他才對我說,“Your predictions for the future are correct in most cases (你對未來走向的大多數預測是準確的)”。後來他又對我說過這句話。
此文篇幅有限,敘事暫時告終。應該說,可讀性頗高,也頗有勵志的意義。我一一寫出來,或許對有志於從事大戰略研究的年輕人有啟發之功用。
就我在斯坦福高端智庫的研究生涯而言,前面陳述的事例截至1991年初。其後直至我2018年底自智庫退休之日,本人經歷過而又值得記敘的大戰略層次的研究課題,還有更多,過程也更精彩,容後補敘。
(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