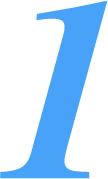山坡上的徐家露台
時間:2021-06-25 歷史與文化
董橋的《橄欖香》,重讀幽香依然。自序裡他說,書裡那篇《玉琮》,“本想好好寫南洋山鄉荷師娘那幢荷蘭殖民地時代大宅院,懂建築的人都說那是古跡,可恨沒有照片,記憶又殘缺,黯然放棄”。未見彩筆細描,爪哇山間那幢荷蘭殖民地時代的大宅院,愈發叫人遐想。
新加坡島上也有不少英殖民時期遺留的老房子,有一陣曾和朋友四處尋訪黑白洋房,有奢有簡,都美,都仿佛藏著縹緲往事。據說島上的黑白屋至今尚留存200多棟,沒想到某年當記者的伏鋼也搬進了其中一棟,他的生活忽而變得讓人羡慕。
伏鋼姓徐,朋友私下喚他“徐少”,像多數人一樣出身平凡,卻是個有福之人。大都會地價高昂寸土寸金,徐少並不富貴,竟能住在一片“都市里的村莊”。小山崗上,大樹蓊蓊鬱鬱,一棟棟黑白洋房散落於蔽日濃蔭。這裡的黑白屋都是平房,大約是以前殖民地中級官員住宅。徐少家的門廊前端,延伸出一方寬大涼台。真正教人羡慕的,正是擁有這麼一處美麗露台。
從前南洋人的生活就是半露天的,微微出汗的。涼台兩面敞開,黑白條的竹簾子半卷起一縷老情調,人坐在清新空氣和植物的味道裡,和蔥鬱的熱帶植被渾然一體。午後島上時常有雨,忽而傾盆,忽而淅瀝,芒果成熟季節,碰巧看到庭院裡青黃果實從樹上飄墜,就像夢中撞見了奇跡。到過這裡的小說家張惠雯寫:“雨停了,庭院裡充滿了黃昏時候澄澈的光線。我在屋裡各處走動一下,發現黑白屋的好處還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結構構成的巧妙光影效果。從窗戶、門廊各處流進的光,在白牆上折射出外頭植物的影子,是這繁華城市裡難得的靜謐畫面。”

(徐伏鋼(右二)和新加坡的攝影愛好者們在庭院展覽、交流攝影作品)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陋室也行啊。”這話出自徐少之口,簡直就是時下人說的“凡爾賽”。但他並不獨享露台,而是把它變成了藝文沙龍,城中文化人聚首之處。鬥轉星移,作家詩人教授,記者編輯主播,畫家攝影家書法家音樂家出版家,都在露台留下身影。外埠來客有的還受邀,在山居愜意小住。
當然出入他口中“寒舍”最頻密的,是一幫“損友”。聚會通常在下午,伴隨一個個隨機話題的,是來自主人家鄉雅安的一盅盅藏茶。有個記者朋友曾納悶,為何唯有徐少能把藏茶泡得那麼濃釅醇厚,沁人肺腑?茶喝得差不多了,不知不覺掩至的暮色裡,眾人的饑餓感隱隱升起,於是茶食水果撤下,換上葡萄酒中國白酒——當然有時這些人從下午就開始喝了,此刻早已微醺——能幹好客的徐夫人親自掌勺的一席川菜家宴,是華彩樂章。赤道晚風涼爽,暗藍夜空下燈火人影,遠望露台,愈發迷人。
有這樣一個清風明月鳥語花香的靜逸居處,信奉“走萬里路”的主人家還是喜歡外出。大學修經濟專業的徐少,和文藝的結緣始於攝影。像有位旅行作家說,“我的雙眼長在雙腳上”,年輕時他駐扎埃及走遍中東,後又在俄羅斯停留數年,遊走世界看過無數自然美景人文勝跡,近年閒置時間稍多,又被神秘的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吸引。對婆羅洲的神往,最先是受了李永平、張貴興、吳岸等人熱帶雨林文學的魅惑。為了尋覓李永平在《大河盡頭》以瑰瑋文字描述的聖山“峇都帝阪”,他六次深入婆羅洲熱土,上下求索,有時一走一個多月。天道酬勤,在路上的風景,撲面而來無窮無盡。
徐伏鋼新書《海島上的家園》第一輯,正是婆羅洲行走筆記。《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守望》,寫只有中學文憑的亞庇“婆羅洲書店”華人老闆,出版家曾昭倫,窮半生精力財力,只為保留珍貴的婆羅洲人文歷史、自然生態文獻,推動有關婆羅洲的研究。
喜愛花草蟲鳥的曾昭倫,早年開店賣T恤時偶遇來自美國的青蛙研究專家英格(Robert Inger),由翻印英格的婆羅洲青蛙專著入手,逐漸結識世界頂尖學者。他創辦婆羅洲自然史出版社,專營野生動植物專業圖書出版,又開Opus Publications,出版婆羅洲歷史、文化、社會學研究著作。多年來推出婆羅洲研究專著200多部,自己也和學者一起合著了《婆羅洲甲蟲大全》《婆羅洲斑衣蠟蟬》,還寫書介紹婆羅洲神山。
揮灑記者本色,徐少挖掘“奇人奇事”之外,文章也富於知識性。很少坡人知曉,被視為“空前絕後”的《婆羅洲蜘蛛大全》一書作者,是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許國豐;本地直腸外科權威蕭俊教授,竟編撰了婆羅洲、新加坡和蘇門答臘竹節蟲專書,彙集20年心血結晶的《婆羅洲竹節蟲分類指南》出版後,大英博物館都得根據他的研究成果,重新調整分類收藏的標本。為許、蕭出版這些專著的正是曾昭倫。
如果說,《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守望》是扎實的新聞特寫,《在婆羅洲島上》則敷染著微妙文學氣氛,尤其第二部分,竟像一個短篇小說的雛形。
“一個黃昏的下午,我獨自坐在臨街一家華人開的茶室喝南洋咖啡。街上人不多,學生早已放學回家,做工的人也都趕著在夜色降臨前行色匆匆四下消散,沿街傳來店鋪劈劈啪啪的關門聲。街面上刮起一陣清涼的風,夕陽從南中國海方向投射過來,金燦燦地印在對面的牆畫上——那是一幅懷舊的電影劇照,舊時代香港大明星林黛和關山主演的《不了情》,特別煽情和招眼。”
開頭這段很有小說氣氛,為全文繪製了場景。婆羅洲島最北端的古達鎮,孤獨旅行者徐少,與仍在咖啡店打發時光的一個華人老頭閒聊。死了老伴,兒子在亞庇打工,孤身生活的83歲老人,忽然對剛剛搭訕了幾句的旅人說:“其實,在我出來之前,家裡是為我娶了童養媳的。”
暮色裡,老人眼睛發亮地描繪那個被他“遺棄”了的“童養媳”的長相,回憶60多歲時回福建老家探親,兩人相處的種種情景,最後,他唱起了湯蘭花的歌,是那次和她一起在卡拉OK聽哭了的《負心的人》……
揣著一顆文學的心走動,才能敏感捕捉到路上邂逅的小人物故事。天涯海角的場景,讓兩個陌生人細細碎碎的對話,有了曠遠悠長的況味,十分感人。
《海島上的家園》上下篇,是徐少兩次踏足沙巴馬布島的記錄。仙本那岸外美若仙境,周圍卻有約兩萬從菲律賓南部島嶼漂流而來的巴夭人,他們在海灘搭建陋屋,或棲身小船,是真正的海上遊牧民族。徐少曾在世界頂級潛水勝地之一馬布島,遇到嫁給巴夭男的日本奈良女大學生順子,身份落差懸殊的婚姻激發強烈好奇,八年後他專程重返,找到順子一家,在與順子夫婦、女兒的近距離接觸中,思索城市和荒島、婚姻愛情與幸福的觀念,也揭示東南亞一角這群無國籍難民的生存困境。全篇以他擅長的特寫手法呈現,有懸念有情節有知識,人物真實細節靈動,是內容豐富的長篇非虛構。

出門,歸來。山坡早晨清新宜人的露台是讀書的好地方,埋首書頁,眼睛裡卻有遠山淡影。不曉得多少文字是在露台的藤木桌邊構思斟酌,潤飾完成。文集裡,讓人印象深刻的另一部分文字,是幾篇人物特寫。
琢磨文字一輩子的董橋總結說,一篇好文章,要有寫意也有工筆。《我對流沙河先生的一點回憶》,是徐少與忘年交,中國名作家流沙河往來的記敘,其中幾段,寫流沙河帶他拜會另一位四川作家高纓,在高家偶遇一個鄉下老木匠,於是流沙河“便與木匠聊起過去自己拉大鋸的事來。哪個樹種最好鋸,哪種木材扭筋倒拐最吃力,兩人話鋒投機,說得活靈活現。聊到興頭上,先生忽然正色起來,說當年他拉大鋸,曾在木頭中鋸出幾顆子彈頭,甚至一次居然鋸出一尊菩薩來……”。
大樹裡鋸出一尊菩薩,簡直是天賜,如此神來之筆點亮全文,已難分“寫意”和“工筆”?
《心月櫻花喜共參——陳瑞獻在京都妙心寺講演揮毫紀實》,寫的是一場“殊緣”。天下如此之大,徐少與太太旅行到京都,竟和應日本政府與世界經濟論壇之邀,在當地參加“世界體育與文化論壇”的陳瑞獻在妙心寺門前不期而遇,確為殊緣。而更深厚悠長的“殊緣”,則發生在陳瑞獻和日本禪宗臨濟派的主寺——京都妙心寺之間:37年前陳瑞獻曾隨廣義法師從新加坡護送六顆佛舍利子來到此處,歸來時他已步入人生秋天,歲月漫漫,其間故事美妙,也正是陳瑞獻在妙心寺對100多位外交官、宗教人士、文化學者和媒體記者演講《坐禪永久》的動人脈絡。演講之後是驚心動魄的現場揮毫作畫,徐少這樣寫:
“一切聲息都沉寂下來,只留下林間的鳥鳴和照相機快門哢哢的聲響。瑞獻先是左手扶紙,忽然一個動作,右手食指抬起伸向天空,再迅速轉而指向畫紙,然後架開馬步踏在紙上,一手捧墨碗,一手握毛筆。一筆落下,頭顱出來了;第二筆下去,濃眉大眼出來了。接下來幾筆,下頷,鬍鬚,對襟,一位仙風道骨的禪師頭像已然顯現開來。這時,瑞獻運筆突然加速,只聽一陣風聲襲來,筆下早已飛流直下拉出一片袈裟來。不料力道過猛,紙破墨噴,筆下突地濺起一團黑色的蓮花來。瑞獻抬起頭來,微笑著說:‘抱歉,紙太薄了。’”
“重新鋪紙,重新落筆。這一次,同樣的風捲殘雲,同樣的龍飛蛇舞,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酣暢淋漓間一揮而就……瑞獻在一片掌聲中直起身來,向大家介紹說:‘臨濟宗創始人,唐代義玄禪師。’”
有條不紊,細節鮮活又富力度之美,像流動的電影鏡頭。讀這兩段忽然悟出徐少筆下常見的畫面感由何而來:習慣通過鏡頭捕捉景物與人的徐少,攝影家的眼睛加持了他的書寫。

(2019年底,大明星林青霞在徐家露台留影)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主角是徐少眼睛裡的大明星林青霞。林青霞由影視圈退隱後一貫低調,多年來鮮見有關她的長篇第一手報導。2019年底某日傍晚,悄然訪新的林青霞忽然降臨徐少山居,讓主人激動難抑興奮慌亂。他描述自己如何以山居周圍為背景,為仍風采照人卻無明星架子的“亞洲第一美女”拍照,如何在露台與女神喝茶聊天,共進晚餐。林間光柔,涼台月淡,一切近在咫尺,又始終如夢如幻。
2020新年,一張林青霞倚著欄杆望向遠方的照片,赫然登上中港台和新加坡報紙,婉約裡的氣派和豔光,宣示了她不敗的美麗和無可取代。攝影者為徐少,拍攝地點正是徐家山居的露台。這是徐家露台的高光時刻。
這本文集可觀處甚多。徐少讀《古寺溫泉》,沾染上杜南發先生文筆的古雅詩意。時隔10年回訪大地震後汶川映秀的特寫,有別於大陸主流媒體的報導,視角獨特。抒寫生活感懷的小隨筆,燒錄作者珍視的點點滴滴。
“百科”類指南上,露台、涼台、陽台,各有不同解釋,無頂也無遮蓋物的才叫露台。總有這樣一個錯覺:八百年前的元夕,辛棄疾“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的“燈火闌珊處”,是一處亭閣或一方露台。
曾經亨利·詹姆斯常去伊迪絲·華頓的“山宅”消夏,在陽台上和朋友竟夜長談。華頓在那本《亨利·詹姆斯》裡寫:“‘山宅'的那些漫長的日子,炎炎夏日,果果秋光,林中的漫步,驅車上山下谷兜風,月夜陽台上的講話,書房爐火旁的誦讀,在我撰寫此文時,又帶著誘人的光輝返回了。”二戰之後的法國滿目蕭條,瑪格麗特·杜拉斯和朋友們常在陽台上聚會,女人們回憶過去的美好日子,聊著聊著,杜拉斯說:“她們在陽台上重建了一個法國。”
杜拉斯把陽台變成了意味深長的隱喻。露台、陽台,往往是一座房子的靈魂。
電影《滾滾紅塵》最動人的一幕,莫過於林青霞踩著秦漢的鞋子在陽台上跳舞,一塊大披巾罩住兩人。這段戲在哈爾濱一棟浸透歲月滄桑的西式老樓拍攝,沈韶華和章能才的原型,是張愛玲胡蘭成。
和張愛玲有關的很多場景是在陽台上,最讓人回味的是:1945年2月某日黃昏,張愛玲在上海愛丁頓公寓的陽台俯視紅塵,生起“這是亂世”的感慨:“……晚煙裡,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小團圓》裡,之雍侄女秀男到九莉住處,九莉和之雍在公寓陽台看她離去,她在街上又別過身來微笑揮手。後來秀男告訴之雍:你倆像在天上。
“文章實難”,董橋說台靜農先生這句是內行話。熱愛寫作的徐少,總覺得自己寫得還不夠好。
何時才能從木頭裡鋸出一個“菩薩”來?怎樣才能真正見到心裡那座瓦藍色的文學“聖山”?永遠文青情懷在露台發夢的徐少的苦惱,不也正是文學絕美的魅惑所在?
徐伏鋼新書《海島上的家園》,即將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工作室出版。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聯合早報》前資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