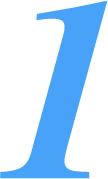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越反越恐”悖論背後,是兩種世界秩序的對決
時間:2021-09-10 軍事與安全
今天的世界被諸多普遍主義敘事及其政治行動籠罩。
2016年4月25日,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在國民議會發表演講。演講中,加尼將塔利班武裝稱為“謀殺犯”。加尼表示,他不再希望能夠通過巴基斯坦斡旋與塔利班進行談判。阿富汗國民安全部隊將會直接著手打擊包括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在內的軍事組織。加尼的演講是近些年來阿富汗政府對塔利班等伊斯蘭軍事武裝勢力最強硬的一次表態。這也引起了來自塔利班方面的強烈反應。4月26日,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即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政權)發言人卡里·約瑟夫·艾赫邁迪(Qārī Muhammad Yusuf Ahmadī)在塔利班官方新聞網站shahamat上發表了一篇講話稿,回應加尼。正如幾乎所有“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話語一樣,講話中,艾赫邁迪採用了二元論修辭方式,將阿富汗聯合政府與塔利班之間的對立視為穆斯林與“異教徒”之間的本質衝突。然而,更有趣的是,在其講話開頭,他將這種身份政治的衝突放在了兩種世界秩序的歷史對抗線索下。他認為,美國對阿富汗的入侵是一條漫長世界歷史線索中的第三階段。在他看來,這條相互衝突的世界歷史開始於11世紀中期,即十字軍東征時期。這條線索的主軸是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烏瑪(Ummah)秩序的不斷攻擊”。其目的是為了“壓制、奴役”穆斯林世界,並對穆斯林黃金時代所取得的勢力影響進行反撲。
從艾赫邁迪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烏瑪不但被理解為一種超世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種現世的政治秩序。它與其它諸種普遍主義世界觀之間,通過政治與軍事衝突,爭奪對世界政治秩序合法性以及世界歷史敘述的解釋權利。這種秩序衝突被稱為西方“對伊斯蘭的戰爭”。而由於伊斯蘭烏瑪是一種終極性的普遍性秩序,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終點,因此這條對抗性的主線可以被用來理解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
艾赫邁迪將這種對抗的歷史分為三個不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從11世紀中期到13世紀末期,這段時期的歷史被十字軍東征所主導。第二階段開始於18世紀,這一到20世紀中期結束的階段被“帝國主義戰爭”所主導。有趣的是,艾赫邁迪將冷戰時期“東方陣營”視為阻擋西方直接入侵的堡壘。隨著蘇聯的解體,老布什政府開始推行“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穆斯林與西方衝突的歷史隨著美國2001年入侵阿富汗,開始了其第三階段。這種建立在穆斯林身份認同上的歷史主義敘事,構成了“政治伊斯蘭”號召力的基礎之一。它用“我們”對抗“他們”這種身份政治的邏輯去理解整個人類歷史,用這種二元論的框架去重述世界的歷史、現在以及未來。
1、“反恐戰爭”定義下的“恐怖主義”
今天圍繞“恐怖主義”產生的一系列話語充分體現了二元論世界觀的深刻困境。而這類討論的產生,則伴隨著上世紀末第三世界社會解放運動的衰落,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的興起。在今天“反恐戰爭”的語境中,“恐怖主義”被視為一種癌症。是與這個現代世界格格不入的反現代者。但同時,它仿佛又是一個當代歷史的創造物,它伴隨著2001年9月11日世貿大廈倒塌的灰燼“產生”於世界媒體面前。這一極具標誌性的誕生故事又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緊密連接在一起。“9·11”事件在這一敘事中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象征意義。無論是在襲擊者還是被襲擊者眼裡,世貿大廈都象征著21世紀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金融核心。2004年1月4日半島電視台阿語頻道中披露的奧薩馬·本·拉登的著名“教令”則更加確認了這種象征意義。本·拉登將這場針對西方世界的“聖戰”稱為一場“我們對抗他們”的“宗教-經濟戰爭”。而他本人,也變成了21世紀這種對抗中,來自世界資本主義秩序邊緣地帶人們最無奈的象征性符號。本·拉登的頭像被制成文化衫、招貼畫、甚至手機屏保,肆無忌憚地出現在蒙巴薩、尼亞美、泗水、白沙瓦、里約熱內盧、卡拉卡斯的街頭。他所代表的這股粗暴的力量,甚至被當作對抗美國霸權的另一種“超級大國”,在那些被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遺忘的邊緣野蠻生長。
與世界“邊緣地帶”出現的這種狂熱相對的,是在今天世界秩序“中心”對“恐怖主義”以及“政治伊斯蘭”徒勞的規訓。“9·11”之後開始的“反恐戰爭”時至今天已經進行了15年。本·拉登也在2011年被正式宣告擊斃。然而,受到這一政策直接影響的西亞與北非地區卻並未因此而平靜。相反,隨著“反恐戰爭”從阿富汗蔓延到伊拉克之後,一股被稱為“伊斯蘭國”的力量卻悄然興起。在幾乎被清繳殆盡的伊拉克復興黨與基地組織的基礎上,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破碎的領土上,建立起了一個試圖實踐“伊斯蘭”政治理想的政權。這當然並非是“政治伊斯蘭”力量第一次展現他們的建國理想。本文開頭談到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則早在上世紀末,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之後便開始嘗試建立起一個民族政府。然而,在面對這兩種挑戰的時候,美國作為“反恐戰爭”的發起者與主導者,卻並沒能提供一種前後一致的可靠判斷。“反恐戰爭”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保守主義者從國家利益出發,對雙重標準的運用。最近的一次案例是美國白宮發言人舒爾茨(Eric Shultz)在2015年1月28日答記者問時,將塔利班定性為“armed insurgency”(武裝叛亂)。與之相對的是被定性為“terrorist group”(恐怖組織)的“伊斯蘭國”。
雖然與“伊斯蘭國”所設想的世界帝國不同,但塔利班這種建國理想以及同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對抗的強烈態度,則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在穆斯林世界中從19世紀末便開始的一場連續性變革中的一個部分。但是,在“反恐戰爭”背景下對“政治伊斯蘭”的敘述卻試圖將其歷史描述為一種特殊的、少數的情況。除了“政治伊斯蘭”這一概念之外,西方知識體系還創造出了諸如“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一系列詞語,試圖將這種穆斯林的政治參與和激進的對抗情緒規訓到某種特殊範疇內。由此希望表明其與“正統”宗教信仰的差異。而在“政治伊斯蘭”話語內部,這種行動卻像是一種“西方帝國主義的宣傳”策略,旨在消磨穆斯林堅定的“鬥爭意識”。
同樣,今天對“反恐戰爭”的批評也被一種相對主義所籠罩。體現這種態度最著名的表述就是“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鬥士”(your terrorist is my freedom fighter)。這句起源於西方流行文化中的虛無主義自白有許多變種。在公眾對“反恐戰爭”的討論中,許多美國左翼中間對里根時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幾乎都陷入了這種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之中。與來自伊斯蘭話語內部那種簡單粗暴,但卻充滿全球野心的歷史主義敘述相比,無論是左翼自由主義者,還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保守主義者們的陳述都顯得蒼白無力。於是,“9·11”之後的世界秩序似乎走向了一個困境。一方面,以政治伊斯蘭為代表的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霸權的反抗,以反現代的暴力方式建立一種以“伊斯蘭”為中心的新霸權秩序。另一方面,在“反恐戰爭”的語境下進行的戰爭行動,則從一開始便繼承了老布什時代美國在全球推行的“世界新秩序”霸權。

(2001年9月11日,世貿雙子塔倒塌標誌美國全球反恐時代到來。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2、階級敘事中的政治伊斯蘭
正如其理論家與吹鼓手們闡述的一樣,“政治伊斯蘭”——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敵人的聖戰觀念——的確產生於19世紀中晚期殖民主義世界擴張的政治現場中。然而,我們也同樣需要註意,與這種以穆斯林認同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敘述同時產生的,還有一種以階級認同為基礎的國際主義理想。而在這種理想基礎上建立起的蘇維埃政權,則對包括大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今天也譯作泛伊斯蘭主義)在內的20世紀世界政治格局的許多普遍主義政治話語都進行了積極的批判。在20世紀,這種理論批判也建立在共產國際從支持去殖民獨立與民族平等運動,到反法西斯的世界革命實踐基礎上。也正是在這種變動中的世界革命現實需要下,共產國際對“政治伊斯蘭”的反帝行動做出了基本批判。
從這種以階級聯合為基礎的普遍主義理想出發,列寧將俄國與土耳其境內興起的“大伊斯蘭主義”定義為“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政治活動。在階級認同基礎上對大伊斯蘭主義進行的批判並不是孤立的兩種認同話語的衝突。它還伴隨著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行動。首先,在一個反對階級壓迫、殖民與財政奴役的政治前提下,對世界範圍內民族平等的強調和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構成了列寧對大伊斯蘭主義批判的基礎。大伊斯蘭主義被視為一種狹隘民族主義的相似物。同時,這種批判的前提還包括“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資源追求聯盟和統一的願望”。此外,在這個世界階級聯盟中,平等是以“消滅階級”為最終目標的政治實踐。
列寧這種在階級平等理想下對民族自決的強調和對狹隘民族主義/大伊斯蘭主義等的批判,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實踐中也得到了體現。雖然,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下,大伊斯蘭主義並未成為一個顯著矛盾。但這並不意味著穆斯林這一宗教身份認同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缺席。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實踐中,對穆斯林群眾的爭取很大程度上被包含在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兩個互通的線索內,並建立在國際層面的獨立自主與和平共處,國內層面的統一與分裂,以及民族身份層面的大漢族民族主義和狹隘少數民族民族主義這三組辯證關係基礎上。而這些都離不開共產主義世界理想中,對建設未來世界平等秩序的追求,以及相應的以階級話語闡釋世界過去與當代秩序的雄心。
3、作為後冷戰現象的“政治伊斯蘭”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冷戰的緩和伴隨著階級話語的退潮,以及共産主義世界革命理想的衰落。而與之相伴的,則是“政治伊斯蘭”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第三世界內的復甦。一些冷戰末期的西方學者為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工具主義的闡釋。“政治伊斯蘭”在第三世界地區的復興被看作是在蘇聯強權萎縮後,地緣政治權力真空裡“弱國家”(weak state)治理的必然結果。還有一些學者用“文化碎片化”和權力日漸分散來描述後冷戰甚至是冷戰後期的世界政治格局特色。
顯然,在蘇聯解體之後,老布什所描述的那種“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並未出現。相反,當時在第三世界中早已開始出現了一系列以伊斯蘭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反西方行動。這種以反帝與反金融霸權為口號的行動,隨著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海灣地區的軍事霸權擴張,而日漸具有了鮮明的反美和反西方特色。這種“失序”在2001年9月11日直接影響到了美國本土。諷刺的是,這正是老布什發表著名的“世界新秩序”演講之後11年。而今天,隨著越來越多來自西方世界內部的年輕人也參與到了這種反西方、反資本霸權的對抗活動中,甚至加入“伊斯蘭國”並對歐洲本土發動恐怖襲擊後,那種將“政治伊斯蘭”視為“弱國家”治理結果的邏輯則顯得無比脆弱。
上個世紀80年代西方學術體系內部逐漸形成的當代國際關係話語,以及在西方政治語境下形成的對當代世界秩序的普遍主義敘述,在今天的“恐怖主義”威脅面前顯得十分無力。而那種在話語層面對“恐怖主義”和“政治伊斯蘭”概念規訓的失敗,也體現了後冷戰時期以美國政治霸權為開端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政治秩序的衰落。事實上,與其站在“反恐戰爭”語境內部,試圖總結出一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不如嘗試從歷史的動態過程中去理解“政治伊斯蘭”作為一種世界秩序的興起與蔓延。行文至此,阿富汗則再次出現,成為我們理解這一變動過程的象征性事件。

(1989年2月15日,最後一任蘇軍駐阿富汗司令格羅莫夫與其子馬克西姆在友誼橋的合影。圖片來源:美聯社)
讓我們將時鐘撥回到1989年2月15日,當地時間上午11:55分。阿姆河上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友誼橋蘇聯境內的那一側插滿了紅旗。最後一任蘇軍駐阿富汗司令鮑里斯·格羅莫夫(Boris Gromov)中將從阿富汗一側過橋,回到烏茲別克斯坦。在橋中央,格羅莫夫中將走下裝甲車,步行穿過國境線,“頭也不回地”向蘇聯一側走來。迎面跑來的,是他14歲的兒子馬克西姆。
格羅莫夫中將是最後一名從阿富汗境內撤離的蘇聯士兵。這天早上,蘇聯對阿富汗長達九年零50天的武裝干涉正式結束。300多名蘇聯偵察兵,乘著數十輛軍車,轟鳴著喇叭,開著車燈,從阿富汗回到蘇聯邊境城市鐵爾梅茲。守候在阿姆河烏茲別克斯坦一側的蘇軍家屬們,在各國記者的注視下,向撤回蘇聯境內的士兵們獻上了他們充滿溫情的歡迎。蘇聯國防部還向所有撤回的士兵們贈送了一枚腕表,以表彰他們的英雄事迹。在簡短的歡迎儀式上,格羅莫夫中將向記者們表示,“盡管付出了犧牲與損失,我們充分盡到了自己的國際責任”。在莫斯科《真理報》2月16日的報道中,也將撤軍描述為士兵們在“盡到了國際主義者責任”後的凱旋。
然而,在在場的其他各國記者的敘述裡,撤軍非但不是一場凱旋,更代表了一種蘇聯式干涉主義的沒落。在蘇聯境內,一種類似於美國越戰時期出現的那種反戰情緒開始蔓延。這種情緒還伴隨著對蘇聯國際主義理想甚至是蘇聯政治體制的懷疑。新華社對此事件的報道中,意味深長地援引了烏茲別克廣播電視台記者加尼耶夫在2月15日慶祝儀式結束時發表的個人感言:“我相信今天的日子將寫在我國的歷史中。這是一場不應該打的戰爭。蘇聯部隊在那裡死傷五萬多人,還有許多戰俘沒有回來。我們本來不應該去那裡,應該由阿富汗人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為什麽我們要作出那麽大的犧牲呢?全部撤軍才是唯一的選擇。”
4、蘇聯撤軍阿富汗
這一充滿了個人主義情懷的評論,似乎很好地呼應了這場奇特的“凱旋”儀式。在龐大的蘇聯共和國裡,那種曾在理想主義氛圍下對共和國戰爭的神聖性崇敬以及對蘇維埃宏大的國際使命的信任,已經漸漸被一種虛無主義侵蝕。與蘇聯國防部向所有最後撤出阿富汗的士兵頒發紀念手表的行動相比,在世界媒體眼中——甚至是許多蘇聯人心中——格羅莫夫毫無留戀地離開阿富汗,並充滿感情地擁抱自己兒子的形象,則更好地代表了蘇聯撤軍這一時刻的真正歷史意義。與冷戰初期那種支持第三世界與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的熱情相比,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關心的是在“新思維”(Perestroika)政策下重振日漸低迷的國內經濟。此時蘇聯人心中更期望看到的是對自身生活與經濟發展的回歸。很明顯,這一讓“阿富汗人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的表述與20世紀50年代亞非拉去殖民運動中對“民族自決”概念的使用毫無共同之處。此時的阿富汗對於蘇聯來說,更像是一個尴尬且沉重的包袱,從戈爾巴喬夫本人到普通蘇聯老百姓,都希望能夠盡快將這個燙手山芋丟開不理。在1986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剛上任不久的戈爾巴喬夫便表示“我們必須要從那裡撤離”,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葛羅米柯也附和道:“這不是我們的戰爭。”在1987年年初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絕望的戈爾巴喬夫毫無掩飾地將這場戰爭描述為“前任領導集體犯下的錯誤”,在他看來,這場“慘重的損失”毫無意義,那些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小夥子”死的不明不白。然而,他也同時意識到,如果就此撤軍,則會對蘇聯“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威信”形成沉重打擊,而且“帝國主義將在第三世界發起攻勢”。
然而,失去第三世界的擔憂並未阻礙戈爾巴喬夫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心。在1987年年底訪問美國時,他向里根表示,“蘇聯人是現實主義者”,他們意識到,阿富汗“有太多非社會主義的特色,例如多黨制、部落主義、資産階級以及宗教教士階層等等”。因此,蘇聯人“不會考慮將阿富汗人變成社會主義者”。只要美國減少對阿富汗伊斯蘭主義反抗組織的援助,蘇聯一定會盡快從阿富汗撤軍,並且停止向尼加拉瓜出售武器。戈爾巴喬夫強調,納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這個一年前剛剛被蘇聯扶持上台的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政府將會做出巨大讓步,貢獻出政府內50%的權力部門,以求能夠同反政府力量共同執政。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已經讓戈爾巴喬夫及大多數蘇共中央政治局中的高層幹部們日漸喪失了對世界秩序的興趣。可以看到,這時期蘇聯政策內卷化在其“新思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項改革充滿了對蘇聯內部經濟狀況的擔憂。在這種條件下,繼續向“不知感恩”的第三世界(特別是阿富汗)投入大量金錢便愈發顯得毫無意義。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蘇聯經濟迅速惡化,商品短缺情況嚴重,黑市物價瘋長。圖為憑票據排隊兌換日用品的群眾。圖片來源:(前蘇聯)塔斯通訊社)
5、作為霸權的普遍主義
在1987年年底的華盛頓峰會中,戈爾巴喬夫向里根提出,由于蘇聯與阿富汗有2000多英里的共同邊界,因此出於蘇聯國家安全考慮,希望戰後阿富汗成為一個不結盟的中立國家。他希望能跟里根進行一個“君子協定”,在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之後,美國也能同時約見反對派武裝,並停止對他們的援助。然而里根明確表示,這不可能。然而,戈爾巴喬夫的決心之大,即便美國未能同意這一重要條件,蘇聯在不久之後仍舊開始著手准備撤軍。實際上,美國對阿富汗聖戰者的軍事援助,從蘇聯最初入侵阿富汗時已經開始。而根據布熱津斯基表示,甚至早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他便建議卡特總統向當地的聖戰者武裝提供武器。他認為,這樣便能提高蘇聯武裝干涉阿富汗的可能,並把阿富汗變成“蘇聯的越南”。即便等到1989年蘇聯真正撤軍之後很久,美國對阿富汗反政府武裝的援助仍在繼續。在1989年2月16日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上,里根的繼任者喬治·布什表示,在美國看來,雖然蘇聯已經撤軍,但是“阿富汗人民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仍在繼續”。美國將會繼續向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裝提供援助。其目的是為了“不讓政府方面在軍事上有壓倒性優勢”。
在上世紀80年代阿富汗戰爭時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相信,伊斯蘭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武器。與蘇聯代表的共産主義世界秩序相比,當時僅僅在局部地區小打小鬧的伊斯蘭力量看上去“危害”較小。在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和1983年貝魯特爆炸案之後,美國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國家資助的恐怖主義”上。在全球範圍內確定了:伊朗、古巴、敘利亞、利比亞以及南也門為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這其中最主要針對的是諸如真主黨、伊斯蘭號召黨(Al Dawa Party)等這類由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力量。以及類似阿布·尼達爾(Abu Nidal)領導的黑色六月等支持巴勒斯坦獨立並反以色列的武裝組織。在美國看來,恐怖主義是一種“政治戰略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幫助伊朗、敘利亞、利比亞這些國家實現其政治目的。因此,最有效的對應方式是以這些國家的利益訴求為基礎,一事一議。這種判斷實際上來自冷戰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與共産主義世界秩序、阿拉伯民族主義,以及來自老歐洲的殖民主義對抗的經驗。自1950年代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便在沙特石油公司的協助下,在沙特阿拉伯東部地區的部落裡,扶植伊斯蘭組織。此外,已知的工作還包括在日內瓦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組織,並策劃對納賽爾的暗殺。
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在1979年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的著名長文《獨裁與雙重標准》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柯克帕特里克強調,美國卡特政府時期在第三世界獨裁國家中強行推行民主化進程的政策毫無效率。在推翻了那些國家的獨裁政府之後,反而助長了強大的反美情緒浪潮。她對“傳統的獨裁者”和“革命共産主義政權”做出了區分。認為前者並不打破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與社會結構,當地居民也在長期的政治生活中,學會了同獨裁者相生相息。因此,沒有必要在這類國家中推行民主化改革。而相反,在革命共産主義政權內,大量人由于革命而流離失所,因此,美國有必要對此進行全面控制。柯克帕特里克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常駐大使,她這一明確的強硬保守主義立場也成為後來對美國外交極具影響的基本原則。
這種站在美國國家利益角度出發,對第三世界的干涉政策隨著蘇聯撤出阿富汗而逐漸達到一個高潮。除了繼續再阿富汗地區支持反政府武裝之外,老布什政府在中東很快便直接投入了一場以打擊伊拉克為目標的戰爭。1990年9月11日,老布什在國會發表其“世界新秩序”演講時無比自信地表示,“最近世界局勢的發展證明,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無可替代”。隨著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迅速放棄其全球視野,美國相信,沒有人能夠再懷疑美國維護全球領導地位的信心與持久能力。此時的美國已經開始了其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武裝干涉。這也是美國自越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全面軍事行動。在短短半年多的打擊中,共有約70萬美軍被送到了伊拉克戰場。

(老布什總統1990年9月11日在國會發表“世界新秩序”演講。圖片來源自網絡)
今天來自“政治伊斯蘭”的恐怖主義活動恰恰形成於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秩序變遷過程中。隨著蘇聯的政治影響及其共産主義世界觀的退潮,以及美國中心主義的世界霸權的擴張,以“政治伊斯蘭”為代表的一系列以民族或宗教認同為基礎的中心主義開始在第三世界興起。而隨著2011年阿拉伯世界動亂而開始的歐洲難民危機,我們也發現,那種列寧所批判的“精致的民族主義”也開始在第一與第二世界復甦。他們或者將自己包裝為對“自由”與“平等”的高尚追求者,或者稱自己為反抗霸權的鬥士。然而,這種面目模糊的“自由”與“平等”正像新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策略性使用一樣,其背後是一種在普世話語包裝下的中心主義霸權。在這種霸權主義邏輯下推導出的國家/民族利益,其核心只能是自利的、反國際主義與不平等的。隨著2003年小布什政府開始第二次海灣戰爭,美國的現實主義者便開始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干涉政策提出了強烈批評。米爾斯海默曾經直截了當地將第二次海灣戰爭稱為一場完全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多余的戰爭”。在一份集合了當代美國最重要的33名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的簽名倡議書中,米爾斯海默等人強調,在針對基地組織而進行的“反恐戰爭”背景下,美國應當通過聯合國等非武力外交手段,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進行全面壓制。而只有在薩達姆政權對美國及其地區盟友構成武力威脅時,才值得對其進一步採用戰爭手段。
從米爾斯海默的批評中,我們似乎能找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內部評價阿富汗戰爭的影子。阿富汗的失敗是冷戰時期蘇聯干涉主義的失敗。在此之後,蘇聯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內建立起的對民族和世界的理解,對現實與未來的信心,都隨著其政治的收縮而漸漸消失。今天,我們也能看到,在“反恐戰爭”背景下的美國干涉主義一步步走向泥潭。站在一個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上,米爾斯海默將民族主義看作“地球上最強有力的一種意識形態”,“無論它何時與自由主義爆發衝突,每次都會勝出”。然而,如果簡單回顧20世紀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米爾斯海默所理解的民族主義——或者用列寧與毛澤東的話來說,狹隘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身份政治認同,並不是永遠處在意識形態的優勢地位。
在這場漫長的現代爭奪世界秩序解釋權利的歷史變遷過程中,狹隘民族主義往往只是在普遍主義平等理想失效的時刻開始瘋長。在今天的“反恐戰爭”中,與狹隘民族主義一同滋長的便是那種以宗教身份認同為中心的暴力。在其宣傳話語中,“伊斯蘭國”被視為一種超越了民族認同界限的理想共同體。而民族國家的出現,則被視為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的惡毒陰謀。在一則紀錄片的訪談中,駕車駛過伊拉克邊境的“伊斯蘭國”“聖戰士”們甚至充滿感情地對著鏡頭表示,這原本被(薩達姆政權的)邊檢、簽證、護照限制起來的“國境線”,在“伊斯蘭國”的治理下,成為真正的“自由”之鄉。人們可以在安拉賜予的天然土地上,無拘束地穿行。他們毫不掩飾自己對賽克斯-皮克協定(注:一戰期間英法俄簽訂的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協議)的厭惡,並將摧毀這一殖民霸權秩序作為自身霸權秩序的合法性論據之一。這種機會主義的反抗與美國那種機會主義式的全球干涉一樣,同樣是霸權主義。它所創造的“烏瑪”神話,也像是老布什在冷戰結束前夕創造的那個“世界新秩序”神話一樣,不可避免地將我們這個世界進一步推向碎片化。當然,正像是一個世紀以前那樣,今天,在世界秩序變動的碎片化縫隙中,一種新的平等理想也許正在生成。
(原發於《經略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