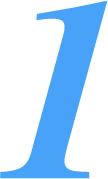阿特伍德,鳥和皮利島
時間:2021-11-19 歷史與文化
1.到皮利島去
9月,我們去皮利島。
就因是安大略省,也是加拿大有人居住的最南部島嶼,在世界第13大湖伊利湖水中貼近美國邊境 ,Peele Island就值得一去?
問剛從島上回來的一個朋友,皮利島有什麽?他說,有一座燈塔是大家都會去的。燈塔?瀕臨三大洋,河流湖泊無數的加拿大,燈塔有近千座之多呢,但他的話讓人想起伍爾芙著名的《到燈塔去》。
雖然去的人不多,島上當然還是有些“景點”的。沒說出我為何對皮利島心心念念,好像懷揣一個秘密:我們去皮利島,只是為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安省很大,不必跨省就夠走的。從多倫多到伊利湖畔碼頭附近,車程三到四小時,但我們中途彎去了和大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有關的埃爾金縣維也納村。
愛迪生的祖父塞繆爾·愛迪生1783年舉家由美國遷移加拿大,1811年到埃爾金定居。生在美國的愛迪生幼年曾來探望爺爺和族親,也在安省西南後來成了戲劇之都的斯特拉福德的火車站工作過。愛迪生的祖父和父親政治立場針鋒相對,都是有故事的人。不過老家已毀,遺址上只見一塊“安大略歷史與考古委員會”立的紀念匾牌。公路邊有箭頭指向“愛迪生家族墓地”。在村裡的Edison Drive走了幾步,寂然無聲。愛迪生博物館也大門緊閉。
離開偏僻的維也納村拐回正道,真的在伯韋爾港撞見了一座有名堂的燈塔:建於1840年的加拿大最古老木制燈塔,塔身裡外皆紅白相間,意外的是還能讓遊客攀著塔內陡峭木梯登頂遠眺,底層設有一個迄今所見最迷你的“遊客中心”。
午餐,戶外飛蟲太多,只能逃進室內。這餐廳的“背景”正是那艘當地政府花了600萬加幣從哈利法克斯拖來的廢棄潛水艇,其間也有一番曲折。一切似無關又有關。一切都是奔向目的地之前的延宕和前奏。這是阿特伍德和她的摯愛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1934—2019)奔馳過無數次的路途,掠過兩人眼簾無數次的風景。近五小時後,我們終於抵達伊利湖邊埃塞克斯縣小鎮的一棟民宿。
天光還亮,這季節白天仍長。因為最近沉浸在阿特伍德長篇《盲刺客》裡,眼前種種都像小說場景。新近修繕的白色兩層百年老屋,寬敞大客廳,地毯優雅,燈飾別致,面朝街道的起居室右側窗口,湖水透過樹叢熠熠閃亮。設施完備,裝潢低調而藝術,看得出主人的品味和誠意,尤其橫貫整棟房子的二樓主臥高敞氣派,正讚嘆著,忽然一個發現讓大家楞住了:偌大窗戶不見窗簾,沒有任何遮擋。
主人來不及裝窗簾就接收住客了,還是小鎮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窗簾無關緊要?這裡餐廳都晚上八點就關了廚房,入鄉隨俗吧。那夜讀到《盲刺客》中一段描寫:
“我從睡夢中突然醒來,心咚咚直跳。窗外傳來丁當的響聲:有人在朝玻璃窗砸小石子……我沒戴眼鏡,卻能看得清清楚楚。一輪滿月懸掛當空,月亮上蛛網般的老紋絡依稀可見。星空下,路燈的光直射雲天,形成一個橘紅黃的光暈。我下面正好是一條人行道,路上影影綽綽的……”
有點詭異。除了沒人砸窗,眼前景象似在印證書裡的句子。
次晨我們趕上了每天只有一兩班,須事先預定的渡輪。這是阿特伍德坐過無數次的船。見過兩張照片,一張在船頭艙內,船長模樣的人向阿特伍德指點著前方。一張是阿特伍德和吉布森倚在船舷,湖上勁風拂過她謎一樣的臉,精靈般的眼睛和頭髮。

(駛往皮利島的渡輪碼頭,寓言似的奇特“鳥山”。余雲攝影)
在船舷回望碼頭,瞬間被一幅圖畫震驚了:一座銀色圓錐體像小型的埃及金字塔,無數白色凸起物長滿刀削般表面,如奇異的大型雕塑。忽而有個白色物體飛起來了,盤旋,離去,其它的仍紋絲不動。
是鳥!天才戲劇演員一樣的鳥群。
寓言似的奇特“鳥山”隨著渡輪起航漸漸向後退去。後來我才明白,鳥,或者說鳥群,正是阿特伍德和皮利島“密接”的一個關鍵詞。
擁“加拿大文學女王”冠冕,阿特伍德的傳記卻極少見,近期中國大陸出版了當地學者撰寫的阿特伍德文學傳記,教人欣喜,但讀完整本書,在其人生中佔據重要位置的皮利島杳無蹤影。
“望著藍灰色的波濤翻滾,望著船後白色尾浪拖曳前進。它像一條撕裂的雪紡綢……”
船將在伊利湖上航行一個半小時。前方那個不大的長方形島嶼——“加拿大好望角”上,遍布阿特伍德和吉布森的腳印,是他們在多倫多之外的第二個家。
2.她在島上數鳥
海鷗,不,是湖鷗追著渡輪飛,阿特伍德坐過的渡輪順著她埋下的“草蛇灰線”航行,一個半小時後抵達皮利島。
從1987年開始,阿特伍德和同為作家的吉布森就在島上有了一棟別墅,他們被視為“皮利島的長期季節性居民”。
阿特伍德寫於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有“女性主義的《1984》”之稱,除此之外,她的最重要小說幾乎都完成於1987年之後。她曾說自己在皮利島完成了許多作品的部分和全部。其中有2000年首獲布克獎的《盲刺客》,2018年重新詮釋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的《女巫的子孫》等等。很多年裡,春天萬物萌發的皮利島上一定有阿特伍德和吉布森相伴的身影,那時節兩人上島倒並非為了寫作,而是來觀鳥,看望那些“長羽毛的朋友”。
皮利島有很多珍稀動植物,也是鳥類遷徙途中重要停靠站,加拿大的400多種鳥類,春季遷徙高峰期,超過一半可在這裡看到。
阿特伍德的父親是生物學家,每年春天進入森林研究昆蟲,入冬前全家返回城市。她才六個月就被帶入森林,幼年大量時間在魁北克北部林區度過。阿特伍德和鳥類的關係可追溯到出世那年,吉布森的野生動物意識卻源自一樁突發的“鷹事件”。看過報道說,60年代某日他散步時和一只嗡嗡作響的鷹不期而遇,“突然,這只該死的大鳥從我頭頂飛過”,“我想,那到底是什麽鬼?”買高倍望遠鏡,讀北美鳥類指南,當他再次發現紅尾鷹時被深深迷住。他覺得觀鳥可達致一種接近狂喜的狀態,將個人意識與身外事物融為一體。1996年不再寫小說後,他以阿特伍德形容的“皈依者的熱情”投入鳥類保護。

(阿特伍德和吉布森在皮利島上。圖片來源:Jane Alexander/QMI)
2003年,阿特伍德、吉布森和一群朋友在皮利島創立非盈利組織“鳥類觀測站”,成為加拿大某個更大觀測鏈的一環。他任主席,她是董事會成員。每到春季,來自各地的旅客一睹紅頸鸕鶿、黃胸鸕鶿和北美的鶯們在渡湖旅程中“降落”休憇,而阿特伍德和吉布森除了搞活動、籌款,主要任務是帶領觀測站成員“數鳥”——沒有準確數字,無法知道鳥類物種在遷徙過程中發生了什麽,而這些信息可讓科學家深入了解生態和環境的變化。
阿特伍德曾描述,人類如果不關心和保護鳥類,海洋和土壤的加速死亡最終會導致人類無法呼吸。一切互相關聯:藍綠藻通過分解H2O來創造氧氣環境,海鳥將糞便排入水中給海藻施肥促其生長……土壤可防止碳釋放到大氣中並有助植物生長,但無機農業“殺死了土壤”,消滅了鳥類通常吃的昆蟲。鳥類,尤其候鳥就像一個預警雷達系統,當鳥類的棲息環境出現嚴重問題並且它們的數量下降,那就是警鐘。
離開渡輪停靠的西碼頭我們先去午餐,這家島上著名的咖啡座,阿特伍德必然到過。一篇2017年的文字,提到77歲的阿特伍德戴著寬邊帽,與穿棕色開衫的吉布森在露台上分享一個三明治。讓咖啡座出名的三明治,果然十分美味。
然後我們驅車去島的另一頭看建於1833年的燈塔。鳥類出沒最頻繁的燈塔區,也是島上主要觀鳥地。我們知道阿特伍德的家就在燈塔所在的島嶼北部,走過林間沼澤中的小路,沿著海灘到達燈塔後,卻並無去尋找房子的念頭。就像安大略西南克林頓小鎮的鄰居自覺守護了愛麗絲·門羅一樣,皮利島居民鼓勵大家觀鳥,不鼓勵觀看名人,阿特伍德燈塔般的光芒,也在島民守衛之下。

(兩座“鳥公寓”精巧別致,讓人想到阿特伍德慧黠的眼神。余雲攝影)
仿佛一種回饋,在據說曾是鳥類觀測站總部的房子附近,我們驚喜地發現了站在一片草地上的鳥屋。金屬藍的天空下青草綠得耀眼,和遠看像兩件裝置藝術的銀色物器,構成鮮明畫面。兩座“鳥公寓”設計不同,精巧別致,讓人想到阿特伍德慧黠幽默的眼神,想到她有發明才能,曾創造出一種能為千里之外讀者簽名的“遠程筆”。
納博科夫一生癡迷蝴蝶,奧康納在祖傳農場養了100多只孔雀,休斯和普拉斯夫婦是養蜂人,村上春樹是愛貓族……大作家親近動物的故事並不匱乏,皮利島上,阿特伍德和吉布森為鳥兒奔忙,卻絕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癖好。
3. 美洲紅鹮與蝴蝶夢
阿特伍德短篇小說集《藍胡子的蛋》裡,有一篇好看的《美洲紅鹮》。小說講述感情已很疲憊的克莉絲汀和唐,帶著小女兒去特立尼達島旅行,和各色遊客坐了一條老朽的船進入紅樹林沼澤看鳥。黃昏,“真的有鳥兒出現了,在發紅的光線裡飛過,開始就一只,接著四五個一群,如此鮮艷,如此光芒四射,像畫出來的火焰。它們在樹中間停住,嘶啞地叫著。只有叫聲才顯出它們是真的鳥兒。”
“唐拉住克莉絲汀的手,他有一段時間沒這麽幹過了……”特立尼達國鳥的稀世景象,點燃了這對中年夫妻間沉寂多時的愛意。
真有意思,為什麽阿特伍德選擇讓美洲紅鹮在小說裡擔任此等角色,只因這種“世界最紅鳥兒”太名貴,是最瀕危的鳥類之一?
實際上,阿特伍德自己也曾問過一連串的為什麽:為什麽契訶夫的劇本被稱作《海鷗》而非《海蛤蝓》?為什麽葉芝如此熱衷於天鵝和老鷹,而不是有趣的蜈蚣或蝸牛?為什麽掛在老水手脖子上的是一只死信天翁,而不是死蚌之類的玩意兒?
自問自答,在2010年發表的文章《行動起來,保護鳥類》裡,她以自己特有的語言歌頌鳥讚美鳥,並說因為父母是自然保護主義者和博物學家,她“一直生活在鳥的世界”,而“羽毛相同的鳥總飛成一群,所以我最終和另一位對鳥感興趣的人走到了一起”。她的吉布森是2003年創立的皮利島鳥類觀測站主席,2006年,兩人更成為國際鳥類聯盟珍鳥俱樂部聯合榮譽主席。
不記得有哪個作家與鳥類的關係如此緊密,從詩歌到小說,從早年的《圓圈遊戲》到2016年的《貓鳥天使》,阿特伍德作品裡的鳥意象不勝枚舉。而這些,僅僅是一個龐大文學世界的微小局部。
是的,一個深刻主題貫穿她的創作。回到多倫多後讀了中國學者袁霞的專著《生態批評視野中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該書將“自然主題:保護生態環境”,列為阿特伍德文學創作的四大主題之一。
那天在皮利島,蠻偶然的,我們走進了一棟與阿特伍德無關又似乎有關的房子。
鎮中心有一排簡易倉庫,盡頭是個連窗戶都沒有的臨時小店,售賣有皮利島字樣的T恤。簡短交談得知,年輕店主夫婦,丈夫來自湖對岸的溫莎,妻子則在島上長大。隨意問了聲還有哪裡可逛,溫莎男說,有個“蝴蝶花園”不錯。
車子開了十幾分鐘來到一棟灰綠色木制平房,門前有片花草稀疏毫不起眼的園地。正疑心是否走錯地方,一個30多歲戴蝴蝶圖案口罩、髮色淡金的女子出現在陽台,說她叫Sharon,這裡接待參觀,家庭收費50加元。
在外邊稍走一會她就帶我們進了屋內,原來“蝴蝶花園”的重點是蝴蝶,真正的“花園”在她家裡。
客廳連著簡易廚房,竈台旁是咬了半截的黃瓜。餐桌上櫃子上,到處有透明的塑膠罐和黑紗網盒,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十分夢幻,Sharon輕柔的手指將罐盒裡的蝴蝶一只只引出,伸到面前讓大家細看,講解一番後又嫻熟地送回。有的蝶剛從蛹裡破繭而出,Sharon讓我們靜觀蝶翅在幾秒鐘裡的微妙變化。她的手指仿佛花枝,花紋精美的藍色、金黃色蝴蝶就長在那手指上。

(皮利島“蝴蝶花園”主人Sharon培育的黑脈金斑蝶。余雲攝影)
Sharon也來自溫莎,原本開了家禮品屋謀生,瘟疫阻斷了遊客,又目賭周圍大片綠草地被發展商鋪上水泥建樓房,心痛無奈。得知島上平房的主人急著賣屋,屋價低還幫忙貸款,兩個多月前她乾脆丟下生意上了島,做自己喜歡的事。
我們走出來時發現,“蝴蝶花園”雖在路邊,四周卻杳無人跡。花草叢中正有幾只蝴蝶盤旋,Sharon說,那是她剛剛放飛的。
不知道吉布森2019年去世後,阿特伍德還經常上島嗎,她是否曉得島上多了個蝴蝶花園?獨自住在“荒野”中孵育蝴蝶的女子,真像是從她小說裡走出來的人物。
天冷了,多倫多家裡已開了暖氣。冬天湖面會結冰,往返皮利島的渡輪將在12月停駛,島民出入只能坐小飛機了。每年都有些島民將離開,待春天才返回島上。
冬天,有些蝴蝶會死亡,有些會聰明地冬眠,有些會遷徙到南方。房內有暖氣,蛹和蝶仍可存活繁衍?那麽,和我們相約三年後再見的Sharon,會在孤島般的平房裡伴著滿屋蝴蝶度過長冬嗎?
真好,美洲紅鹮和蝴蝶夢;真好,阿特伍德,鳥,皮利島。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