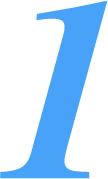我經歷的“中壢事件”(二:鋒芒畢露)
時間:2022-01-05 歷史與文化

(我如願進了《中國時報》,從1971年11月22日起成為要聞記者,每天在這張桌子上振筆疾書,不知寫了多少字。圖片來源:優傳媒)
“毛遂自薦”如願以償
正當苦於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不知哪來的靈感,想起了毛遂自薦的故事。於是就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余紀忠先生,表示有興趣參與新聞工作,並附上幾篇作品。沒想到馬上被余先生接見,面談之後,就輕而易舉地進了《中國時報》。我希望到採訪組當記者,但因採訪主任比較有個性,不太喜歡余先生直接交下人馬,余先生就先把我放在編輯組,他告訴我:“採訪組現在沒缺,你先到編輯台,也好看看編輯台的作業情況。”我在編輯台待了三個月,跟著一些年紀非常大的老前輩學習。編輯台這段經驗,使我提前知道了編輯老爺對記者們的評價和看法,非常有用。
1971年11月22日,我正式開始當記者。在這之前,採訪主任張屏峰先生約見了我,他說:“聽說你來了一段時間,也知道你是臺大的優秀人才,我們早就想借重你。”又很客氣地說:“歡迎你加入採訪組,但想請問你,你有沒有特別希望採訪什麼樣的新聞?”我心裡屬意的是政治新聞路線,最好能跑國會或外交,這可都是主線,需有相當資歷和表現的人才有資格,我再愣頭愣腦也不好自己開口。於是我說:“我沒有一定的主張,完全看報社用人的需要。”他說:“這樣好了,也不是考你,我出三個題目,不教你怎麼做,你自己想辦法做,寫成報導也好,專欄也好。寫完給我,再來決定路線。你看好不好?”他出的三個題目是:第一、“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的重大任務”。第二、“如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第三、“如何突破當前的外交困境?”。

(採訪主任張屏峰先生是我最信服的長官,面冷心熱,是非分明。他帶領我踏上要聞採訪之路,後來卻因我而受到人事衝擊,以為出自我的暗中算計。在我遠走他鄉多年後他才知道,其實我反而因極力護他而開罪老闆,為了這天大的誤會,他竟正式向我道歉。一位真正的君子人!圖片來源:優傳媒)
從外事切入,為國大暖身
這三個題目都屬於政治類,且與國會和外交有關,竟然跟我心裡想的一模一樣。重要的是,這些無不是攸關國家走向的大題目,報社難道要把這麼重要的大事交給我嗎?不免有些忐忑。接令之後,便即刻開始籌劃回答這三個題目,先交了兩篇,在第三篇還沒交的時候,採訪主任叫我明天正式上路。明天是11月22日,一一二二,數一數二,好記,好兆頭!此後就開始了我在《中國時報》的新聞生涯。
畢竟是新人,報社並未即刻給我太重的採訪路線,何況比較大的各個採訪線都已經有人負責。採訪主任交給我的任務是:第一、國民大會明年初春開議,要我先去接觸國大代表(那時有1300多人),從認識這些人開始,進一步認識國民大會的功能(後來證明,這是他非常有遠見的安排);第二、外交部的外圍單位,包括世亞盟(世界反共聯盟、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救總(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僑委會等這些外交部的外圍機構。這兩個路線,既有政治部分,也有外交部分,要我先從周邊開始進行新聞採訪工作。
第一天專訪了來臺訪問的日本勝共聯盟(國際勝共連合)主席久保木修己。他是世盟邀來的客人,通知我們去採訪。當時《聯合報》派的是陳祖華兄,《聯合報》的大牌資深記者,差不多大我10歲以上。訪談之後我回去就寫了一篇邊欄,第二天在第二版刊出。世盟的新聞聯繫人唐子維先生故意刺激陳祖華說:“祖華,你看看,人家剛剛上路就寫了一篇大文章,以後你們可要小心了!”上崗第一天,就讓人眼睛一亮。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表現亮眼,名字頻頻見報
當時記者寫新聞通常就是“本報訊”,沒有記者名字;但是寫邊欄或方塊,就可以署名。我通常在不署名的新聞稿發完後,總有一些分析或觀察性的材料,經採訪主任認為有價值,就可寫成邊欄,便會以“本報記者周天瑞特稿”或“本報記者周天瑞專訪”的方式登出來。結果,我三天兩頭(甚至往往連續幾天)就會有一篇邊欄見報,產量高得令人傻眼,這對於記者打開知名度很有幫助。沒有多久,交通記者離職,報社便將交通線交給我。11月開始跑新聞,12月就接下交通線。交通部是重點部會,涉及很多相關的機構,同時還兼跑木柵的考試院,以及繼續接觸國大。
我不是一個只會把人家的新聞資料拿來抄抄寫寫,發“本報訊”的人,我也不是一個為出風頭愛寫專欄的人。我能很快受人注意的原因是,跑新聞非常勤奮迅速,很有衝勁,相當具有敏銳度,會自己找題目,能在採訪中看到特別的角度,並且有很好的表達力。
1972年2月20日至3月25日召開國民大會,是六年一次的重頭戲,報社可以派兩名文字記者採訪。原來跑國會線的記者是當然人選,另一個人選是誰便很受矚目,對這種重要露出的採訪機會,每個政治新聞組的記者都會有所期待。這一回大家早已經看出了苗頭,除我之外應不作第二人想。答案揭曉,果然由周天瑞入選。

(活躍於國大採訪之餘,偷閒在議場(陽明山中山樓)外與國大會務主管(抱歉,名字不記得了,哪位能告訴我 ?)合影留念。圖片來源:優傳媒)
經營國大有成,接下國會新聞重任
國民大會開會期間,主跑的郭人傑兄負責“新聞索隱”方塊,側重從議題看國大。我負責寫“國大側記”,那種一則一則集起來的邊欄,如果寫得不好,很容易流於亂七八糟的花絮。我不想變成這樣,就從探討國民大會的歷史開始,講他們以前的故事,進一步探討一些現象,這是很多人原先不知道的。藉著一篇篇的國大側記,我把似乎不是很主要的議題處理得很熱鬧,很有可讀性。慢慢到進入正式議程的時候,我還從議題上去側寫他們開會前前後後、裡裡外外的情況,以及學者專家的反應。包括從議題討論當中看出什麼微妙,從中做些比較深入的觀察。比主跑的內容還豐富。
因為我在國民大會開會前後跑得很勤,跟國大代表有了頻繁接觸,又加以做足功課,國大代表各種派系、小團體上上下下那麼多人,我都熟得不得了,他們看我就是個有出息的年輕人,很喜歡和我來往,因此交了不少“老”朋友。我的外公就是國大代表,但是我從沒找他問過一個消息。他看了我寫的東西,經常鼓勵我:“瀋陽呀,你怎麼知道那麼多事情啊?”(我在瀋陽出生,長輩都喚我瀋陽)我的表現讓他覺得很有面子。我從不向他問東問西,一來不要讓他為難,二來走內線不是真本事,三來我廣布的消息來源告訴我的材料還寫不完哩。
國民大會一個月的會期,真正討論議題的時間並不多,因此要每天晚上寫一篇“國大側記”,還真要花不少心思。當時在國民大會上,有許多學校提供的大學生來為國代服務,東吳、輔大、文化都有,大都是政治系的學生,我跟他們也混得很熟。他們告訴我:“我們老師說《中國時報》的‘國大側記’,你們一定要好好讀,很有內容。”可見我把國大的專欄經營得有聲有色。
國大採訪,碰觸禁忌初體驗
有關中央民意機構改選或廢除國大的議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是完全不能碰觸的,然而這個問題已逐漸浮現,政府也打算在當時的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多藏一些玄機,已備日後運用,但是老國代堅壁清野、高度警覺,因此在國大議場暗流洶湧。這是很敏感的話題,在言論受到控制的當時環境,不容報紙有絲毫觸及與點破。但我難安於“無功能”,於是設法透過文字技巧,既能掌握分寸,又能帶出不能寫的東西。比如點到為止、意在言外、暗埋地雷等等,偷渡一些訊息、諷刺或批評,這就是所謂的“曲筆”,讓明眼人心領神會,看出蹊蹺,但又不直接對沖到禁忌。近代史泰斗沈雲龍教授(他也是國大代表)曾當面誇讚我“曲筆”寫得有功力。此外,我並首開風氣之先,時常拜訪林山田、胡佛、李鴻禧等憲法學者,借他們的口說自己想說的話,跟他們頻繁接觸;甚至後來引進他們在《中國時報》寫專欄,宣揚民主憲政思想和憲政主張,對民主改革有相當的影響。
國民大會是在陽明山中山樓開會,所以每天一大早搭車上山,傍晚散會趕回報社發稿。一個晚上要寫不少字,到了11、12點下班回去倒頭就睡,第二天又一早起來,周而復始。這樣緊湊的生活,過了一個月。國民大會結束後,報社就把整個國會新聞線交給了我,扛起要聞大旗。
採訪國會新聞的感受
這次國民大會除了行禮如儀,完成蔣介石、嚴家淦連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以外,最重要的是修訂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老成凋謝而基於“法統”需要“國會不能全面改選”的情形下,增加國會名額,在新產生的立、監委、國大代表之前冠上“增額”二字,以達到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目的。於是,在我正式採訪國會一年後,第一次增額立法委員(約51位)開始進到立法院,其中有:康寧祥、蔡友土、黃澤青、謝深山、劉松藩、蕭天讚等人。那時還沒有王金平,他是1975年第二次的增額立委。
國會新聞路線是指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這三個中央民意機構。國大每六年召開一次,平時基本沒事,但立、監兩院經常行使職權,尤其立法院,每天開的會不比今天少,而遠比今天認真。儘管不似現在有那麼多政黨矛盾,但國民黨內的派系較勁,立法院與行政院的意見衝突,乃至立委與黨中央(蔣介石)之間的相左,也都是經常發生的事。並且,由於國家所有的政策都要在立法院變成法律,立法過程就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用心的記者有取之不盡的題材可以學習和發揮,得到很大的成長。所以立法院是個政治大場域、新聞中心,是非常重要的採訪路線。但當時只由一個記者照顧整個立院新聞,倘遇監察院開會,還需兩頭奔忙,任務之重可想而知。

(蔣經國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有一天中午休會後,走到議場前面與國會記者們打招呼,臨時起意,就在議場台階上席地而坐,留下了這幅開心的畫面。圖片來源:優傳媒)
那時候《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較勁得相當激烈,國會新聞尤其是主戲,我和我的對手顏文閂幾乎每天在比賽,一個晚上就要發出好幾千字、甚至上萬字的稿子,報紙的一、二、三版新聞經常由我們包辦,二、三版還要看我們作文比賽(邊欄)。比新聞鼻、比角度、比深度、比文筆,又要比處理技巧。白天採訪的時候,密切關注對方的動靜,第二天早上一打開報紙,首先看對手幹了什麼好事。偶爾偷閒一起去三重看場小電影,還得暗自提防對手明天的“報上見”。我常說,只有商人和記者真的天天在打仗,而記者更有著強烈的好勝心和榮譽感在其中,因為他們的名字會見報。我和對手相互競爭,也相互敬重。

(老立委張子揚就是老國會時代的典範之一,“老賊”二字斷不會出自我口。圖片來源:優傳媒)
以我採訪國會的經驗,在那個所謂“老賊”(我採訪當時還沒有這個詞語)的時代,我深為不少老立、監委的見識和風骨所折服。他們有的很肯研究法案;有的總是為民請命;有的鉅細靡遺,字字推敲;有的犯顏直諫,堅持原則;有的儘管不敵權勢也要留下國會紀錄。他們力抗威權所表現的錚錚風骨,嘗令我感動落淚。他們不是庸碌之輩,對早年的國家政策和立法有相當大的貢獻,相信當年浸淫國會的人都從他們身上受益很多,包括曾與老立委共事的黃信介、康寧祥。我一直以為,將整個時代的荒唐、謬誤與錯亂,全盤歸咎於他們,乃至對他們極盡羞辱和摧殘之能事,絕非公道,這樣的做法,必不配蒙受祝福而得享永久之福澤。
作者:周天瑞 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
(原發於台灣《優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