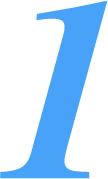觸怒僑務,一篇“檄文”引發的慘案(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六)
時間:2019-08-16 歷史與文化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六。
---------------------------------
永遠要知道,任何產品應以消費群體的需求和利益為最大考慮,《美洲中時》既然落脚美洲,就應有“美洲心情”,縱然不能完全達到,起碼要使人有感。這不叫討好,這叫懂事。
走過一年,有了嘗試和驗證,美洲心情格外浮現而趨具象。前文所說的周年感言,既說不以第三者而以當事人看自己,又言應以有利於未來在美生根為重,少受來自母國政治左中右獨的干擾,便是兼顧“所來”與“所在”的念想。
既然是念想,便不盡存在於現實,這樣的念想自會與現實碰撞,不可能不發生遭遇戰,以致受傷。很快地,它就來了。
兩岸中國人在海外都有一種行當叫“僑務”(“華僑事務”的簡稱),國民黨在這個行當裡,有一種公職叫“僑選立委”,就是從華人的居地產生立法委員。在人家的土地上不好大剌剌地辦選舉,因此它的產生不由普選,乃由遴選——由政府在華人當中挑。
可想而知它會怎樣地在僑界造成紛亂,為了爭奪由政府施予的名位,會怎樣地助長各種人性的醜陋,會怎樣地製造一堆矛盾。往往每經一次遴選,就留下一大片狼籍戰場,難以收拾。為了免於繼續為害,早該檢討這個不祥之物,最好廢掉。
1983年8、9月的遴選作業又要開始了,舊金山灣區有兩位新僑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有意競逐的人發表政見,增加大家對他們的認識。意思無非是,這個早受詬病的制度是否起碼該做一點改變,讓想要拿這個職務的人不再只是面對提拔他的長官,轉而稍稍面對置身四周的華人。
這個想法其實很低調,但有意思,想不到僑務委員長毛松年卻斬釘截鐵以四個字回應:不以為然!
他是遴選工作委員會的召集人,這麼一說,等於把這個建議當場槍決,毫無可斟酌之餘地。
這種反應肯定不合人心,我即刻撰文評他的“不以為然”,針對此公所說“不以為然”的三點理由一一批駁,末了還“加柴添火“地說:
似毛松年之談話,既乏以民意為念之胸懷,亦不諳為官之道的訣竅,......聽在身處開放環境的眾多僑民耳中,實為標準的無學養、無邏輯、無說服力的官腔官調,更遑論蕴含在此種論調中那保守落伍的氣韻。
《毛松年式的話語,請休息休息吧!》,老編用了最後一句話做成主標題,高挂第三版,異常醒目。
 (1983年僑選立委遴選作業開始,舊金山灣區有兩位新僑希望有意競逐的人發表政見,想不到僑務委員長毛松年卻不以為然。作者供圖)
(1983年僑選立委遴選作業開始,舊金山灣區有兩位新僑希望有意競逐的人發表政見,想不到僑務委員長毛松年卻不以為然。作者供圖)
刊出的同時,並即刻在同版開闢了《僑選立委意見廣場》,提供公開園地,聽聽大家的意見。從當日起連續了一個月,藉此徹底把這個制度做了一次檢討,各方反應非常熱烈,所提意見非常寶貴,很是難得。毛松年為此發了4000字專文回應這些意見,但一個意見都沒接受,什麼改變都沒發生。我陸續以《請正視海外對立委遴選工作的聲音》、《評毛委員長<海外遴選立委答客問>》等文前後呼應,表達:“暮鼓晨鐘豈能充耳不聞?”、“蕭規曹隨無以開創新局!”和唯有“博採周諮才能四海歸心”等諫言,對於毛松年長達4000字回應意見廣場的答客問,我也毫不客氣地批評回去。
所有這些意見一如“狗吠火車”,說了等於沒說,說了等於白說。然而,時至今日,僑選立委安在?它在不分區立委中勉強保留着名號,但各政黨都擺在名單後段,根本進不了榜,以致名存實亡。在目前的立法院裡,叫僑選立委的一個都沒有,僑界也就清靜了不少。而這是我們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大聲疾呼的主張。
國府方面是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這場遭遇戰的,否則毛松年不會以4000字回應,因此可視為《美洲中時》與台北方面的第一次對撞,也是台北方面對《美洲中時》第一次明示不滿。只是這個事件沒有直接傷到時報當局,因為,所有咎責全由我吸收了。
原來,批評毛松年式的語言,本是擬以社論發表,總主筆很客氣地徵詢我是否不做社論而改做專欄處理,我即刻會意。大家應還記得,總主筆陳裕清先生長年主掌海外工作,毛松年這些僑務主管他焉得不識,經他手發此稿的確為難了他。因此,有關這個事件的處理,從新聞,到民意廣場、評論,再到專欄,便由我一鍋端,循總編輯這個系統,下發工廠上到報紙,他只當不曾與聞了。
開明如他,沒有阻止這篇稿子,已是難得。而總編輯這邊也沒皺眉頭,每回都順利放行,不時還大呼過癮。
不久,外面有反應了,裡面也有反應了。別忘記,余紀忠用了不少有海工會、新聞局、黨部背景的人,不知道是裡面的人透過外面呢,還是外面的人透過裡面,反正一來一去,一搭一唱,相激相蕩,壓力就到了余紀忠那裡。
余紀忠一看,是周天瑞署的名,他事前也確實不知道,這不正好嗎,可想而知他會怎麼說,以内部發落給擋掉了。到了内部,余自然會問,想知道總編輯怎麼說,社長怎麼說,他們一看情况不妙,當然推給了署名的人。
那社長更絕,竟好似理所當然地加上一句:“我還叫天瑞不要寫,他就是不聽!”絕不誇張,就這麼回事。這都是我後來聽說的,有人看不慣,便自然傳到我耳裡。
我不怪誰,愛做,沒得怨,連解釋都不必解釋,我全部吸收了就是。
然而這卻使我在《美洲中時》的處境陷入谷底,為我那時惡劣的心情加踢了一脚。
翻閱1983年下半年的每日記事(備忘式的記錄,算不上日記),經常出現這樣的字句:“睡眠情况太差”、“這兩天都沒睡好”、“又沒睡好”、“只睡了兩小時”、“睡了一天,仍甚疲倦”、“睜眼到天明”。1983年12月11日竟有這樣的記載:“今服鎮靜劑半粒”。我一向抗拒藥物助眠,這一天顯然已堅持不住,服了半粒。直到今天,用藥睡覺,這是僅有的一次。
還有這類字眼:“甚無趣”、“今日心情奇壞”、“心情仍然壞”、“近日頗多煩惱”、“終日奔忙不知所為何來”、“想回台北”、“想辭職”、“不想做了”。
“睡眠不足”、“心情不好”。這是我在《美洲中時》最困頓的一段時間。
先說睡眠不足。
《美洲中時》是後生晚輩,為了迎頭趕上,連出報時間都有計較。為了可以容納中港台每天中午以前的重要消息,還可以領先各報大半天進入市場,我們出的是早報,有別於其他華文報紙中午以後出報。所以我們的作息時間和在台北差不多,只是比台北更晚一點,紐約編輯部大約凌晨兩、三點人去樓空。
這正是台北開始忙的時候。有一些台北母報可能需要的内容,要為台北發過去,還有時報雜誌另外需要的供稿,也要幫忙邀了發過去,甚至執筆寫過去。這些事沒有配置專人做,又不好調遣別人熬大夜幹這無償之活;而我與台北淵源深,他們習慣找我,逐漸便成了我的工作。在忙過美國這邊的事以後,接着獨自一人留下來幫忙台北,為此工作到清晨六、七點是常有的事,有幾回還搞到九點。
大白天才睡覺,睡眠品質本來就不會好,而當地的事也不會為我減少。何况開會、規劃、聯繫、會客、邀稿、採訪、寫稿,甚至不時出差,本來加在身上的事就多,一天下來,能東拚西凑幾個小時睡眠?加上壓力重,心情又不好,就更難好睡了。
好在我的身體素質經得起熬,過去在台北就有“鐵人”之稱,睡眠不足還能對付。但是睡眠不足加上心情不好,就成惡夢了。
再說心情不好。
我在11月11日(一年後的這一天關報,何其巧合!)給楚崧秋先生的信上有這樣的記述:日積月累,心中之事不能傾吐,現實之缺不能稍除,鬱悶煩憂交加,誠不知何以為繼?
 (《美洲中時》停刊聲明。作者供圖)
(《美洲中時》停刊聲明。作者供圖)
楚崧秋先生是較之陳裕老後一輩的文宣領導,也更見儒雅開通,是我在台擔任中時採訪主任時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特別投緣。9月底,他曾來信關心我,我隔了近兩個月才回他此信,對這位心儀的長輩說說心裡話,首次向他提到離開時報或請調回國的想法,意在請益。但因他和余先生交稱莫逆,信中雖表示“伏請以私信待之,必勿宣諸余先生之前”,仍擱置了八天,直到11月19日才付郵。
付郵的時候,除了原信之外還加寫了一個後記之類的“附言”,向楚公敘明之前留中未發的情節,近日幾經思考,決定自我砥礪,以更多耐性和智慧,苦撑下去,使之步入正軌。所以請他把這封信中剖白的心情當做一段已成過去的歷史,這樣我就不避諱那番“赤裸告白”了。
也就是說,等我想通了,心情好轉了,才把信寄出去,不希望毛躁行事,讓長輩為我擔心思。從處理一封私信都有這樣的瞻顧,經受這麼多琢磨,可以想像我必遭遇了好大的難處。
1983年10月下旬,“華視新聞廣場”(中華電視公司的政論節目)來美製作《美洲中時》專題,由我全程協助主持人陳月卿,提供資訊、安排採訪。因我對一切瞭若指掌,陳月卿自然希我入鏡受訪,我也絕對勝任愉快,但我全部給了裡裡外外的人,堅決不接受一個take,她至今可能都不明所以。
那是我心情最不好的時候,不願露臉,且讓余先生他們在畫面上看不到我,他們自己去猜想,也由得外界去奇怪吧。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延伸閲讀】
中時遭暗算,報人余先生要把自己送出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二)| 周天瑞
“遭逐”兩年後空降中時,難逃“被害”命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三)| 周天瑞
It is not fair!從美東喊到美西(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四)| 周天瑞
“有所為而為”,不做海外第三者(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五)| 周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