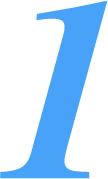感受俄羅斯:我家住在江那頭
時間:2019-10-21 俄羅斯
【編者按】三策智庫網自今日起,將陸續發表上海外國語大學學生在“全球重大事件多語種全媒體報道”課程中,以中俄建交70週年及中俄關係為主要選題的佳作。三策智庫雖主要聚焦來自新聞界專業人士的聲音,但同時也將目光和希望寄託在優秀的青年人身上。此次登載青年習作,旨在為他們提供一個展現新聞理想以及溝通交流的平台,望讀者用包容和發展的眼光看待並給予建議、鼓勵。同時,感謝曹景行老師為《青年習作》欄目作序。
我們為什麼會去俄羅斯
先說一件三年前的小事。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美國總統大選之日,我們所在的賓州州立大學已是深秋。寒風細雨的午夜,校園裡已經沒有什麼人。賓州正是決定勝負的最關鍵搖擺州。形勢對特朗普越來越有利,校內學生絕大多數支持希拉里的早就心灰意冷陸續散去。學生活動中心HUB的大廳裡只剩下我們幾位來自中國的學生,仍然關注著電視直播的選情變化。結果,第二天當地報紙頭版大選報導,用的照片竟然就是電視機前的我們的學生。
那年,我們可以說是在現場看著特朗普當選,就像八年前和四年前看著奧巴馬當選和連任一樣,當然不是同一批學生。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重大事件多語種全媒體報導”的課程始於2008年,今年已是第12個年頭。每年我們從全校優秀學生中再選拔出20名外語和專業能都很不錯的尖子,到當年世界上發生大事的地方去採訪報導。去年以阿根廷的G20峰會為主題,前年是法國大選和泰國國王葬禮,今年輪到了俄語專業,選題就是中俄建交70年和當前中俄關係。
我們的課程已經成為上海市高校優秀科目,但最重要的成果是參加的學生在短短兩三個星期內的快速成長。作為老師,我們等於是把那些基本上沒有新聞經驗的大孩子,一下就推到國際新聞採訪報導的第一線,與世界各國最重要的媒體和資深記者踏上同一個舞台。結果,本來不會開口提問的孩子,突然變得自信起來、勇敢起來,在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面前會感到以往從來沒有過的興奮。更辛苦的是每日每夜反復修改稿子和視頻,擠掉了他們一半以上的睡覺時間,最終拿出還算可以的作業。
下面幾篇是我們的公眾號第一批發表的,最後拖慢刊發速度的,不只是俄羅斯網速本來就慢,更是因為從那幾天往國內傳送視頻竟然遇到新的屏障,不得不用迂回的辦法讓國內同學幫忙接力轉發。還有其他作業跟著會來,有請各位以資深新聞人的眼光給他們打分吧。

哈巴羅夫斯克,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交界處東側,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首府。對於中國人而言,它有一個更加熟悉的名字:伯力城。
伯力城曾是中國達斡爾部落的世居地,也是明、清兩代的固有領土。清朝後期,在《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和《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簽訂後,伯力城歸沙皇俄國所有,並以17世紀侵略黑龍江流域的俄國殖民軍頭目哈巴羅夫而得名“哈巴羅夫斯克”。
漫漫的江水,隔開中俄兩國,為哈巴羅夫斯克這座邊境小城的人口、歷史和文化賦予多元的魅力。哈巴羅夫斯克的記憶不是單單由斯拉夫民族構成的,更是多民族共同記憶交織繪製而成的。百餘年過去,哈巴羅夫斯克仍與中國保持著若即若離、一衣帶水的關聯。

(阿莫爾河落日)
瓦洛佳 - 80歲 - 翻譯
“我有兩個祖國,都同樣讓我自豪”
初見瓦洛佳是在領館門口的長椅上。他和他的太太清(化名)坐在陽光下與路過的人聊天。瓦洛佳長著一張亞洲面孔,卻有一雙湛藍的眼睛。我猶豫半天,走上前問他:“請問您會說中文嗎?”瓦洛佳哈哈一笑,說道:“當然,我是北京人呢。”見我面露尷尬,他又接著說:“我是中俄混血,我母親是俄羅斯人。我們已經在這裡生活五十年了。”
瓦洛佳沉默了很久,突然很認真地看著我說:“人們總問我,更喜歡俄羅斯還是更喜歡中國。實際上,我一直覺得我有兩個祖國,都同樣讓我自豪。像我們這樣的人總是被人逼著做出選擇,好像如果說兩國都喜歡就是虛假。我掙扎了很久,不停奔波中俄之間,想要找到平衡,卻發現唯一的答案其實很簡單。我愛中國,也愛俄羅斯。而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兩國的和平穩定相處。”
旁邊的人突然插話道:“瓦洛佳可是哈市大名鼎鼎、受人尊重的翻譯呢,他還曾經給很多大人物都做過活。”
瓦洛佳打斷他:“我們不是什麼大人物,不能像政府官員、企業高管一樣做出決定性的貢獻和改變。只能從自己能力範圍可以觸及的方向入手,盡一份力。”
清挽住他的手。他們相識於國際廣播電台,結婚已經超過四十年。“他還當過紅軍呢,蘇聯時期全民徵兵,瓦洛佳也去過。”她突然有些激動,拉住我們,“他真的為中俄交往做出很多努力。”

(哈巴羅夫斯克金頂教堂內)
迅 - 85歲 -倒貨商人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迅長著一張很歐式的臉,高鼻樑,藍眼睛,看起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俄羅斯人。招待會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和迅四目相對有一點尷尬,我對他笑笑。他叫住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知道北大荒嗎?”
我點點頭。
“你知道知青嗎?那些年在北大荒,從上海來的知青一批又一批。看到你們就又讓我想起那個時候,一晃又是四五十年,時間過得真快啊。”
我有些迷惑,“您什麼時候來俄羅斯呢?”“那時候文化大革命,我被趕到北大荒,又從北大荒逃來哈巴。我在北大荒還做過老師呢。剛逃到俄羅斯的時候也沒什麼好做,只有倒貨。和大老闆一起。貨物一箱一箱從北京拉到俄羅斯。情況好的時候,沒運到莫斯科就全部賣完了。碰上蘇聯解體,盧布匯率不穩定。前一天才進五百美金的貨,第二天就只值五分之一的價格了。難啊。至今回想起來仍然讓我感到絕望。俄羅斯人根本瞧不起我們,就叫我們黑毛豬,黑毛豬。走在路上提心吊膽,生怕一不小心就會被人搶。”
“我已經快八十五歲了,快樂或者不快樂也沒什麼重要的。而且你看看她。”他把他身邊的俄羅斯女孩推到我面前,“她是我孫女,她甚至不會說中文。我想回去啊,可是我該怎麼回去呢?”
“她生活中所有都是用俄語進行的,學校,工作,沒有人說中文。我倒是想教她啊,可是從何教起呢?”他長歎一口氣,“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START’起跑線)
苗雲(化名)- 55歲 - 服裝生意老闆
“30年後,我的夢想終於成真了”
苗雲一定是招待會上最耀眼的女性。她穿著富貴的祖母綠長裙,搭配著全套碧綠的玉飾。當我終於鼓起勇氣走到她旁邊,闡明來意,她豪邁地笑著說:“你叫我苗姨就好了。”
“我是90年代末期來俄羅斯的。一開始生意真是難做。資金就是大問題,沒有資金,沒有技術,只能從倒購開始,回國批發服裝,用不起火車就只能一點點從國內把貨物拎過來。你知道‘拎包客’嗎?說的就是我們這樣的人。不過啊,你可不要小瞧拎包客,我認識的不少大老闆都是從拎包開始的。一點點,一點點,像螞蟻搬家一樣,積攢多了就有了資金啊。有了資金就可以慢慢開始自己的公司。現在做生意就容易很多,可以貸款啊,但那時候連貸款都是沒有的。還有就是安全問題,蘇聯剛解體時真是不安全,回家路上就總能看見有人躲在暗處,一不小心就會衝出來搶你。現在沒有了,安全了很多。”
“一開始來俄羅斯當然不好過,語言不通,那時候俄羅斯人總是高高在上,是看不起咱們的。總覺得前十年真是難,別人總覺得咱們是來這裡逃荒的,做的事情也不體面,形成不了氣候。後十年慢慢變好。一是因為咱們這一批螞蟻搬家的人很多後來都成了大老闆,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祖國越來越強大,現在走在路上也沒人找我麻煩。我覺得現在挺好的,我們一家人都生活在哈巴。”
“我退休了。我的女兒在哈巴開了一家酒店,兒子開了建築場。所以我就放心地退回家裡了。種種花,沒事和朋友小聚一下。其實我最開始工作的時候目標就是為了養花,哪有女孩子不喜歡花的呢?30年後我的夢想終於成真了。”

(哈巴羅夫斯克街景)
阿妍(化名)- 23歲 - 留學生
“俄語翻譯是一件很體面的事情”
招待會上呈現出的不僅是中俄建交70周年來的風雨兼程,更是這70年來哈巴的眾生眾像。歷史的痕跡,生意的往來,似乎都太沉重了一些,幾次交往後便覺得筋疲力盡,心裡湧起深深無力感。我決定逃離一小會,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四處觀望,我找到了那個屬於我的地方。走過去才發現還有另外三個竊竊私語的女生,亞洲面孔,禮服華麗,舉著高腳酒杯,大而靈動的雙眼透露出對這場招待會的興奮與好奇。我小心地從人群中穿過朝她們走去,嘗試著用破碎的俄語問:“你們會說中文嗎?”三個女生猶豫了一會兒,齊齊點頭:“我們從撫遠來,在哈巴羅夫斯克的大學交換。”
“感覺和這邊有語言障礙嗎?”
三個女生不好意思地笑道:“有的。我們從撫遠來,才剛來一個月。我們從高中就開始學俄語,但說得還是不太好,俄語真是太難了。遠東地區有很多東北來的留學生,因為離東北很近嘛,我們那從初中就可以選外語是讀英語還是俄語。隔著一條黑龍江,商貿往來特別多,很多人寧肯不讀英語也要讀俄語。我就選了俄語,希望有一天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去莫斯科工作,然後回家鄉當一個翻譯。翻譯這個工作可體面了。”
“其實我覺得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真的挺友善的。雖然我們俄語說得不太好,但平常交流的時候,他們會不停鼓勵我們,還誇我們講得好。老師上課也會多用簡單的語言,讓我們也能聽懂。至少這一個月來,所有俄羅斯人對我們都還是很友善的,沒有碰到有歧視性的事件。”
“我還是想回家去的。但是我也想看看,這個講著我學了快十年語言的國家到底什麼樣。”

(上外報導團採訪當地居民)
結語
我們在哈巴的第一天就看到了黑龍江。寬闊的水域在落日的餘暉下金光閃閃。我們坐在江邊,看著江水波浪平靜,江對面熟悉的燈光點點,那是我們的,是瓦洛佳的,是迅的,是苗姨的,也是在俄千千萬萬華人華僑的故鄉。中俄關係的變化和影響,在他們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從中蘇關係蜜月期,到關係緊張,再到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歷史的軌跡千變萬化,洪流推著人們往前走,迫使他們做出選擇,也給他們提供機遇。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一路上,我們總是聽到各色各樣的人講:“中俄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重大事件多語種全媒體報道”團隊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