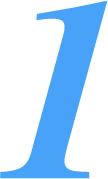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德國問題” 再現 歐盟處於歷史緊要關頭
時間:2020-05-28 歐洲

(2020年5月18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頻新聞發布會。圖片來源:路透社)
5月1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達成了一項重要的共識,倡議設立規模為5000億歐元的歐洲經濟復甦基金,由歐盟出面舉債,在未來歐盟預算中償還。雖然此前歐盟已經出台了5400億歐元的援助計劃,但是這一新的舉債計劃卻是突破性的進展。此前,意大利、法國等國提議設立“新冠債券”遭到德國的否決,而這次設立的經濟復甦基金,朝著共同債券邁進了一大步。為什麽在自己的任期即將謝幕的時候,默克爾邁出這一突破性的一步呢?根本原因在於“德國問題”再次成為德國必須解決的問題,歐盟處於一個歷史的緊要關頭,如果法國和德國不能再次攜手,歐盟在內外挑戰之下,面臨生死考驗。當然,歐洲的聯合是在一個又一個歷史緊要關頭中闖過來的,危機倒逼改革也是歐盟不斷走向聯合的一條經驗。
“大德意志” 還是“小德意志”?
歷史的發展如同一條河,有水面如鏡的平湖,也有飛流三千尺的瀑布,決定河流方向的就是緊要的關頭,歷史演變也是如此。我們去書寫和研究歐洲的歷史的時候,也不會面面俱到,而是選擇關鍵的節點。歐盟現在是不是處於一個歷史的節點呢?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對歐盟的衝擊不亞於2009年歐債危機,加上2015年的難民危機,三重危機疊加而形成了系統性的危機,這對於歐盟現有的結構構成了尖銳的挑戰。新冠疫情之下,歐盟各成員國基本是各自為戰,而疫情見頂之後,復工復產需要攜手,意大利等財政比較緊張的國家提出發行新冠債券,實際上是變相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樣的訴求在歐債危機的時候也出現過,但那個時候,默克爾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十年過去了,歐盟似乎陷入了戰略的迷茫期,缺少明確的身份定位和戰略構想。
新冠疫情對歐盟是一次壓力測試,就像一座房子一樣,能不能經受住地震的衝擊,除了地震釋放的能量之外,就看房子的質量,如果是一座本來就有裂痕的房子,必然受損嚴重,甚至是坍塌。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讓歐共體變成了歐盟,但不能不說,歐盟是早產兒,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以後的“歷史終結論”的樂觀情緒之下,歐盟快速擴張,耗盡了歐洲一體化積聚的能量。在《馬約》之前,歐盟算是一個直營店,此後以加盟店的戰略,快速擴張,而歐盟內部的制度建設遠遠沒有跟上擴張的速度,內部的離心力越來越強,尤其是在危機時刻,“脫歐”變成了成員國自保的策略。“德國問題”是歐洲一直面臨的問題,而歐盟是“德國問題”的答案,德國只有融入到歐盟之中才能消解“德國問題”,這是德國人在探尋“德國問題”的過程中的一條經驗。從德國統一之後,歐洲的歷史緊要關頭都與“德國問題”糾纏在一起。“德國問題”的本質是在歐洲體系之下能不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容納作為民族國家存在的德國。
研究歐洲國際關係的學者得到的基本共識就是在歐洲現代國際體系興起的過程中,德國的分裂是這一體系能夠存續下去重要的前提。從17世紀以來,歐洲大陸紛爭不斷,英國能夠作為海島國家采取“光榮孤立”的政策,其前提就是德國沒有建立起現代主權國家。法國大革命之後,民族主義高漲,德意志民族要建立統一的國家,擺在德意志邦國面前的任務有: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的邊界在哪裡;德意志國家的主權構建問題;如何與歐洲體系共處下去。
俾斯麥通過鐵血政策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他選擇的是“小德意志”的方案,沒有將奧地利包含進來。現在來看,俾斯麥是明智的,“小德意志”方案不僅表示德國的領土訴求是有限度的,更重要的是德國統一之後還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戰略。在統一之後的近半個世紀中,德國與歐洲國家基本相安無事,維持了和平,為德國的發展創造了比較良好的國際環境。這是非常難得的“和平崛起”。威廉二世沒有俾斯麥的視野,更無法理解“德國問題”的歷史邏輯,放棄了“小德意志”的戰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突破了德國作為歐陸國家的限度,德國從根本來說是個陸權國家,缺少海洋的思維和歷史智慧,並不是建造軍艦就可以成為海權國家的,從後來的戰爭來看,德國的海軍幾乎是擺設。
一戰之後,魏瑪共和國是個悲劇,德國還沒有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同時疊加了民主政治,尤其是在戰敗的陰影之下,“小德意志”的方案失敗了。第三帝國興起,不僅要在歐洲大陸擴張,還捲入到了海權與陸權的搏鬥。二戰結束之後,德國被四國分區占領,後來出現了兩個德國,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承認了東德,“德國問題”暫時得到了解決。當然,聯邦德國的構建其實是英法美賦予的,聯邦德國成為冷戰的前沿,歐洲一體化、北約將聯邦德國納入到了大西洋體系的網絡之中,“德國問題‘的三重內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德國在歐洲一體化中扮演了沉默的貢獻者,悶聲發大財,所謂的法德軸心不過是德國搭台,法國唱戲。冷戰期間,德國實現了重新崛起,但是從來不表現出領導歐洲的意圖,德國的崛起是遮遮掩掩的,也是和平的。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柏林墻的坍塌,讓“德國問題”再次浮現,聯邦德國總理科爾將《十點聲明》提交給聯邦議員,但是他沒有跟法國總統密特朗進行過任何溝通,也沒有跟其他西方大國商量過,而這份聲明將德國重新統一作為目標。密特朗威脅科爾,法國可以像一戰之前那樣聯合各大國來圍堵德國。“大德意志”,還是“小德意志”?科爾其實選擇了後者,一是沒有改變邊界,尤其是與波蘭的邊界;二是不改變德國與歐洲的關係,將法國恐懼的德國經濟實力交出去了,推動構建歐洲貨幣聯盟和政治聯盟。歐元,其實是穿著馬甲的馬克,是德國統一付出的代價,連科爾也承認,歐元是個早產兒。貨幣一體化其實從70年代開始就出現了,原因是歐洲國家無法忍受美元“囂張的霸權”,但是在德國統一的時候倉促推出,歐元先天不足,沒有共同的財政基礎,統一貨幣無法將各個成員國籠絡在一起。
從冷戰結束之後,歐共體變身為歐盟,走上了”加盟店“的快速擴張時期。我們可以用廣度、密度和深度來衡量一個組織或者體系,冷戰之後,歐盟為了廣度而犧牲了密度,同時深度的缺失讓歐盟進入了瓶頸期。
廣度,歐盟的成員國快速擴張,2004年歐盟一下子吸納了八個成員國,這是一次”大爆炸“一樣的擴張,曠日持久的土耳其入盟談判意味著歐盟的邊界可能在幼發拉底河,這是一個超級歐盟,這個人造的歐盟已經把歐洲撐破了。密度,歐洲一體化從煤鋼聯營開始,到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到貨幣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互動密度不斷提升,新吸納的成員國雖然也有門檻,廉價航空以及高速公路網絡提升了互動的密度,但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深度,其實就是認同的問題,中東歐轉軌國家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加入到了歐盟,政治制度、法治水平、權利觀念以及歷史經驗都與西歐不同,甚至說,中東歐國家並不是文化意義上的“歐洲”。
歐盟“緊縮” “德國問題”再現
冷戰結束之後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突進的十年,可以說全球體系的廣度、密度也得到了極大地增進,歐盟和北約雙重東擴。歐盟的擴大,在客觀上為重新統一後的德國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德國問題”消弭在歐盟擴張之中。無可否認的是,歐盟擴張造成的廣度、密度和深度的不匹配,甚至是摩擦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弭。危機到來的時候,原形畢露,歐盟凱歌高奏的日子在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之後戛然而止,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入了危機十年。歐盟的擴張結束了,“緊縮”的歐盟體系讓崛起的德國難以遮掩,“德國問題”再次出現。俾斯麥、阿登納、勃蘭特和科爾等等這些在歐洲和德國“歷史緊要關頭”做出抉擇的德國政治家逐漸積累和形成了德國的戰略傳統,即“小德意志”的方略,有原則的妥協求得與歐洲的協同演進,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柔性崛起的道路。
2009年歐債危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根本一條是沒有財政聯盟作為基礎的貨幣聯盟是有結構性缺陷的,面對華爾街的金融風暴,美元沒有倒下,歐元幾乎被打趴下了。為什麽會這樣呢?第一,歐元作為“早產”的非強勢貨幣成為歐洲聯合的工具,而不是水到渠成的成果;第二,《馬約》規定的貨幣聯盟的門檻基本不可實現,債務占GDP比重在60%以下,赤字率控制在3%以下,其實是體現了德國的經驗和訴求,尤其是經歷過20世紀20年代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後,德國財政紀律是最為嚴格的歐洲國家之一;第三,歐元區擴張過速,希臘是依靠財務造假而進入歐元區,成員國的差異性暫時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被掩蓋下來,潮水退去,才發現誰在裸泳。

(圖片來源:路透社)
歐債危機暴露出了歐盟或者歐元區內部的南北之爭超過了東西差異,北方集團和地中海集團之間的矛盾是尖銳的。作為財政紀律優等生的德國堅決反對為南歐國家提供救濟,在希臘,默克爾被畫成了希特勒的形象,還要向德國索賠二戰的損失,足以看到德國與希臘等國之間的矛盾和分歧。
“德國問題”的焦點不在於德國自身的國家構建,而是德國的邊界以及德國與歐洲如何共處。德國的領土邊界不會調整,但是經濟邊界已經變化,尤其是借助歐元,德國成為出口的發動機,德國人也承認如果沒有共同貨幣,德國對歐元區國家的出口不會如此迅猛,歐元運行十年,歐元區形成了中心與邊緣的分化,德國人生產,南歐人享受,歐債危機最終讓這種模式難以持續下去。
德國是歐洲的德國還是歐洲是德國的歐洲,這個問題在兩德統一的時候出現過,依靠貨幣聯盟暫時消弭了這一質疑,十年之後,德國的實力難以掩蓋,德國堅決反對發行共同債券,更不願意建立財政聯盟,換句話說,德國還沒有準備花錢購買和平。2012年,歐盟27國中的25個國家簽署了《財政契約》,這並不是財政聯盟,而是進一步強化原有的財政紀律,要求各國逐年削減負債率。當然,在應對歐債危機過程中,歐元區也創造了歐洲穩定基金,為處於危機的國際提供貸款,這算是歐元區的一次系統升級,修復了一些缺陷。值得關註的是,歐元區負債率在2019年下降到了84.1%,尤其是德國低於60%。歐元是穿著馬甲的馬克,那歐元區能變成大號的德國嗎?
歐債危機似乎已經過去了,尤其是希臘退歐危機逐漸消弭之後,人們不再太關註歐元區的問題了。歐債危機的影響是巨大,回到十年前,歐元區內政治震蕩,默克爾是在這場危機考驗中屹立不倒的政治家。南歐國家就不用說了,領導人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雖然沒有引發政變之類的劇變,但是對選舉民主是很大的損傷,自由民主解決不了經濟危機。危機進一步稀釋了歐盟共同的價值觀,沒有加入歐元區的東歐國家也沒有動力謀求加入其中,尤其是匈牙利、波蘭等國以“非自由民主”來挑戰歐盟的價值觀。
危機共振 歐盟處於歷史緊要關頭
歐債危機折射出歐盟的戰略迷茫,歐盟是作為一個經濟組織,還是要成長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治最重要的功能是利益的分配問題,歐盟內部的實力結構已經處於失衡的狀態,尤其是時任法國總統的奧朗德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意願讓法國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歐債危機余波未平,難民危機來襲,與歐債危機不同的是,這一次默克爾扮演了領導者,甚至是獨斷者的角色。2015年9月4日,在歐盟的“歷史緊要關頭”,默克爾邁出了一大步。2015年9月初,數以千計的難民從布達佩斯沿著高速公路步行向奧地利邊境進發,這一場景在社交媒體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奧地利總理法伊曼給默克爾打電話,希望允許來自匈牙利的未登記的難民進入奧地利和德國。默克爾只是與內閣中的社民黨的同僚進行了溝通之後就答應了這一要求。
2015年9月,歐盟面臨著難民危機的衝擊,默克爾沒有與歐盟以及歐盟成員國進行溝通就做出了決斷,事實上突破了“小德意志”的戰略傳統,影響或者破壞是巨大的。

(2015年9月1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探訪難民收容所時,與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自拍”。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一是默克爾事實上僭越了權限,為歐盟做了決斷,但沒有與布魯塞爾進行溝通。9月10日,默克爾訪問了柏林的一處難民之家,與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自拍”,智能手機將這些照片傳到了互聯網上,默克爾成了“默克爾媽媽”,這是默克爾以及德國的“高光時刻”,問題的關鍵在於德國以及默克爾光輝形象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第二,難民危機之下,歐盟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抉擇就是確立邊界問題,尤其是難民有可能登陸的南歐國家,如果不加強歐盟的邊界管控,歐盟成員國之間就會面臨邊界管控的問題。德國的“歡迎”政策,讓難民湧入德國,在德國引起了強烈的政治反彈,選擇黨這一反移民的政黨迅速崛起,東歐國家反對德國的難民政策,尤其是匈牙利拒絕接受非基督徒的難民。
第三,難民問題暴露了歐盟一體化過程中回避的身份認同問題,也就是關於“深度”的問題,東歐國家沒有多元異質文化共處的經驗。德國對難民的歡迎政策,事實上打破了歐盟的文化邊界,何嘗不是“大德意志”的戰略思維呢?德國接納了上百萬來自異質文化圈的難民,出現了一系列的摩擦,甚至是恐怖襲擊,雖然德國政府不承認這是恐怖襲擊,但是即便是德國,也無法在身份和文化上擴大自己的邊界。
第四,難民問題是歐盟的分解劑,在歐盟的東西兩端都出現了“脫歐”的傾向,英國脫歐從卡梅倫的政治投機變成了英國的政治災難,東歐國家更加尖銳地挑戰德國的權威。在“脫歐”的風潮之下,德國也有擺脫歐盟束縛的思潮,如果德國也脫歐,將是歐盟的毀滅。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內部的權力結構大變,歐盟更趨向於陸權集團,另外,法德之間缺少了英國的緩衝,德國的責任是更加尖銳的問題。德國學者就認為,“英國脫歐之後,從表面上看,德國因其人口規模和經濟實力方面的分量在歐盟內領導地位會更加突出,但其實英國脫離歐盟一事最大輸家就是德國。”
緊縮的歐盟襯托出德國的強大,是走“大德意志”的道路,還是回歸“小德意志”的戰略呢?德國近代一百年多年的經驗是“小德意志”的戰略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皮膚,國家不能超越自己的時空。2016年以後,默克爾就在調整戰略,彌補戰略衝動帶來的損失,加強歐盟邊境的執法和管控。2016年英國脫歐、土耳其巨變基本界定了歐盟的邊界。德國學者認為,“對歐盟而言,從與土耳其的入盟談判中所學到的教訓是:地緣戰略上的擴張是有其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其所觸及的國家在政治上和價值規範上的身份認同。一種無視這個道理的擴張政策並不會讓共同體變得更強大,恰恰相反,它會讓歐盟變得空洞並走向毀滅。”
2017年馬克龍上台,他是一個堅定的歐洲主義者,對歐盟的定位是“地緣戰略力量”,相比於馬克龍激進的歐盟戰略,默克爾是中庸之道的回歸。特朗普上台之後,大西洋兩岸的裂痕不斷加深,美法德三方之間的互動,界定了歐盟的限度,以及大西洋體系內部的關係。新冠疫情是歐盟面臨的突如其來的外部衝擊,與已有的危機形成了共振,歐盟再次處於“歷史緊要關頭”,只是因為這場疫情危機已經全球化了,美國是重災區,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歐盟面臨的危機。
法德共同倡議設立規模較大的經濟復甦基金,是默克爾做出的重大的妥協,也是“小德意志”戰略的回歸。當然,德國也會防範馬克龍的戰略衝動,過度消耗德國的實力。一個比較理想的戰略圖景是德國與法國攜手夯實歐盟的密度和深度,放棄冷戰結束後二十年的過度擴張。然而,這其中面臨的一個悖論是,回歸歐洲大陸的歐盟如何在大西洋體系中扮演合適的角色,歐盟的邊界在硬骨脫歐之後回到了英吉利海峽,更重要的是與英美代表的海權系統之間的分離。
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一個殘忍的現實是,美元的地位非但沒有削弱,反而不斷加強,疫情之下的“美元荒”說明了美元是世界經濟體系的貨幣基礎,美聯儲成為全球性的最後貸款人,美聯儲與世界主要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之後,美元荒才得以緩和。相比於美元,歐元在結算、儲備領域大幅度回落,德法意三國國債的總額只有美國的一半,只有德國國債是AAA。馬克龍的雄心壯志需要德國實力的支持,歐元依然是穿著馬甲的馬克,沒有這件馬甲,德國缺少緩衝,硬崛起帶來的是障礙,甚至是遏制。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有句名言說,在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往往是達到目的最短的途徑。
(作者是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