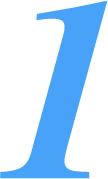回歸廿三載:香港不可成中國推普死角
時間:2020-07-03 港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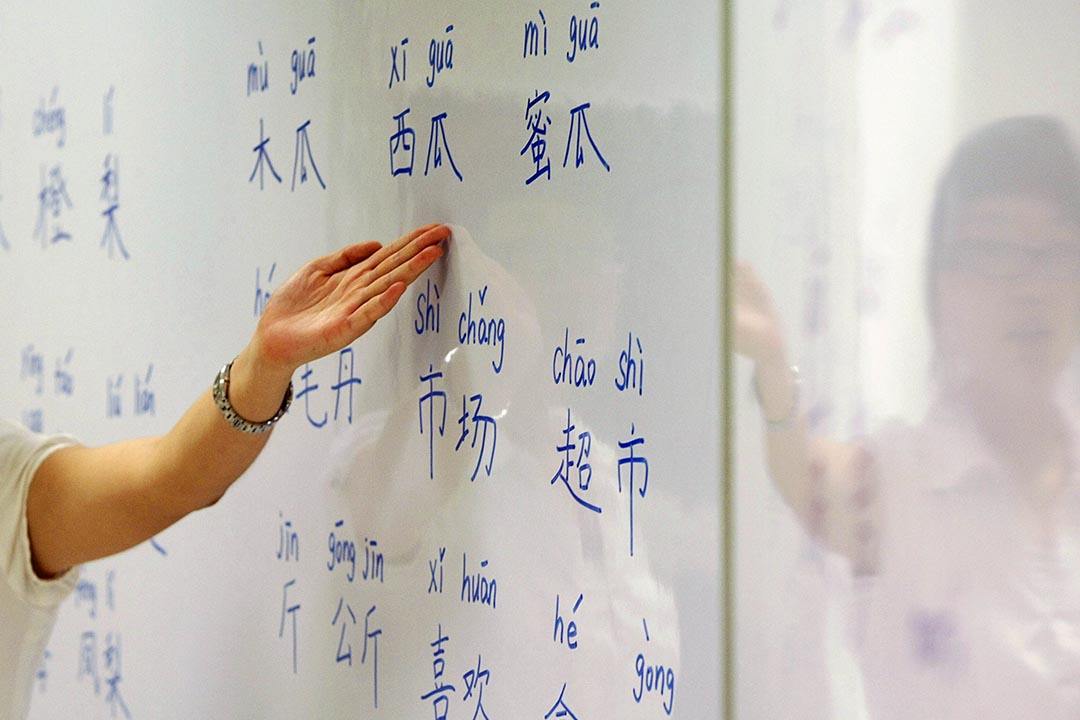
蘇聯的主要締造者、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列寧(1870年-1924年),在《論民族自決權》一文中說:“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這一論斷揭示了語言的社會本質和重要作用。語言不僅是每個人須臾不可或缺的溝通工具,而且是每個人的資源與武器。
人們從牙牙學語開始,就在學習語言。香港人大多從小就學會說廣東話,廣東話也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只是由於它是一種方言,並不是全國通用的共同語;全國通用的共同語是普通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同年10月8日,特首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書第84節中提出:“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1999年10月6日,他在第三份施政報告書第69節中將基本法第九條之規定概括為“兩文三語”。他說:“特區政府的一貫宗旨,是培養兩文三語都能運用自如的人才。”
“兩文”指的是書面語,即中文和英文;“三語”指的是口頭語,即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兩文三語”是香港的語言政策,也是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培育香港人(特別是學生及就業人士)兩文(中文、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的能力”是香港中文教育的目標之一。
中文是中國的語言文字,特指漢族的語言文字。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其書面形式就是標準中文(Standard Chinese)。中文和普通話是“一國”的標志;英文和英語是“兩制”的標志。“三語”中的粵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書面形式之一是“港式中文”(Hong Kong Chinese)。香港一位教授說,“港式中文”是一種“混血語言”、 “怪雞文體”,看到這樣的文章,不能不慨嘆“中文之衰落,良有以也”。
令人欣喜的是,香港回歸那年,董建華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書第84節中就確定了具體目標:“由下學年起,我們會把普通話列入小一、中一和中四的課程;我們也會在2000年底前,把普通話列為香港中學會考科目。”令人失望的是,香港的莘莘學子中學畢業後,竟然大多不會講流利的普通話,不諳漢語拼音,使用電腦和手機時,大多不會用拼音輸入法。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香港的大學都開設普通話選修科,而教學居然是零起點。掛大學的牌子,用大學的資源,開設中小學已經修讀過的課程,豈非咄咄怪事?原因何在?
一是在基礎教育階段,普通話和中文分家。本是一家人,卻硬要分開過日子。在香港,中文科用廣東話教,亦即所謂“廣教中”或“粵教中”。中文課本中所選的白話範文都是標準中文,但教學語言卻是方言而不是共同語。環顧周邊國家或地區,唯有香港如此。
由於中文和普通話分科教學,後果是二者不但不能互補,相輔相成,反而是中文科拆普通話科的台。比如識字教學,只能口耳相傳或采用粵語拼音方案。中文每周五六節,普通話每周一兩節,學生在課堂上所學的幾句普通話,到中文課上,立馬被廣東話抵消殆盡。“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二是在香港,家庭用語、社會用語、教學用語、校園用語、廣播用語、影視用語、辦公用語、櫃台用語甚至報刊用語都是廣東話。特區政府在社會上不推廣普通話,社會上看不到推普標語,倒是可以在商鋪門口看到“我們會講普通話”的揭示語。那些會說普通話的銀行職員、商店售貨員、酒店和餐飲業侍應生、旅行社導遊等“就業人士”,都是靠口耳相傳或業余惡補習得的。
學習任何一種語言,如果缺少語言環境的浸濡(immersion),是很難習得的。而今日之香港,廣東話依然一枝獨秀,傲視普通話。在這種環境下,青少年怎麽能學好普通話呢?
這種現狀特區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門難道不了解嗎?不是。那又為什麽不思改變現狀呢?因為他們在思想上沒有擺正“一國”與“兩制”的位置,或者不客氣地說一句,在某些特區官員及公務員的靈魂深處,“兩制”淩駕於“一國”之上,而且他們還會理直氣壯地擺出《基本法》第136條作為“護身符”。13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不錯,《基本法》確實賦予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教學語言政策的權力,可是特區政府千萬不要忘記本文前述所引有關憲法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條款。特區政府在“自行制定教學語言政策”時,是否認為這些條款不適用於香港?是否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無論口語還是書面語都無需規範化、標準化?“一國兩制”的“兩制”是否容許廣東話永遠一枝獨秀?香港的中國人是否可以永遠“語不同音”?
在香港,有些政客故意將工具性的語言文字政治化,用心十分惡毒。曾幾何時,某兼任大學教席的女議員曾批評前特首梁振英在講話中整天用“方方面面”“重中之重”等“內地用語”,並表示她為此“深感憂慮”,擔心“內地用語成為統戰工具”。可是,這位女議員難道沒有看到改革開放後“靚”“減肥”“埋單”“T恤”“跌眼鏡”“鹹魚翻生”等一大批“正宗港詞”湧進“大陸詞匯”嗎?這又該如何解釋呢?該不是在搞“反統戰”吧?

香港人如果不健忘,應該記得,2012年7月1日上午9時,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本屆特首的就職典禮在程序上與往屆無甚區別,唯一亮點是梁振英在致辭時用普通話發言,無須翻譯。他不但發音正確,而且音色淳美,不帶廣東腔,給筆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第一印象。其實梁振英“兩文三語”都“好叻”。香港特區政府中的高官能用如此動聽的普通話在這麽重要的場合發言,相信梁振英是第一人。
在香港,還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凡是在由香港主辦的國際會議上致辭時,如果會議用語是漢語,那麽他們大多講廣東話,寧可在有需要時配普通話通譯員。廣東話淩駕於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之上,儼然成了香港特區的“區語”,這已成為不成文的規定。在國際交流場合,中國人講中國話還要翻譯,這樣裝樣子,滑稽不滑稽?
特區政府的官員們有機會輪流到首都最好的高等學府參加短期普通話培訓班,可是學成歸來,卻不思推廣。更令人不齒的是有人故意不講普通話,硬用廣東話為難自己的同胞。據報道,邊檢職員在與內地入境旅客發生爭執時,竟有勇氣大聲說:“我聽不懂普通話!”你“聽不懂”,你得學;“大佬”!你是一線公務員,請你聽懂了、會說了才上崗。
2003年7月,內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開通,從當時的4個城市逐漸增加到49個,覆蓋2.5億人口。2018年訪港旅客入境人次超過6514萬,其中內地訪客達5080萬,日均十多萬人。他們大多操普通話,這在客觀上對香港社會層面的推普是極為有利的,然而特區政府熟視無睹,我行我素,依然不重視在社會層面大力宣傳、推廣、普及普通話,打造講普通話的環境。何也?當權派心知肚明,“唔使畫公仔畫出腸來啩”。
正是由於回歸23年來特區政府不在社會上大力推普,而學校裡的普通話教學又收效甚微,因此自“佔中”事件以來,特別是在去年6月發生的“反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街頭接連出現令人發指的現象。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對到港自由行的內地同胞尋釁滋事,以“蝗蟲”稱呼他們。更有甚者,他們圍堵內地遊客,用廣東話唱《蝗蟲歌》,當眾羞辱他們,而在旺角、尖沙咀等地發起“驅蝗行動”,嚴重傷害了內地同胞對香港的感情。在這場風波中,“反中亂港”分子還多次當街滋擾、毆打講普通話的遊客或在港工作人員。有個台灣記者疑因說“國語”(普通話)而遭圍堵,情急之下大喊:“我是台灣媒體,不要攻擊我……”
今年5月,全國政協13屆三次會議於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13屆全國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先生提交了一份《關於加強民族地區、港澳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的提案》,提及要在全國20%未普及普通話的地區推廣普通話。

香港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被譽為“東方之珠”,竟然屬於“全國20%未普及普通話的地區”,特區政府顏面何在?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3年,怎麽還沒有把語言運用標準化、規範化提上議事日程呢?“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對特區政府而言為什麽那麽困難?難道有什麽難言之隱不成?對此,特區政府必須深刻反思。
“港區國安法”足音跫然,“反中亂港”分子的喪鐘已經響起。香港“再出發”時,決不能當全國推普的死角,必須急起直追,大力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23年折太多,病樹前頭萬木春。
(作者是香港資深語文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