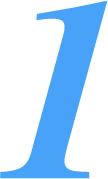普拉斯和伍爾夫的衣櫥
時間:2020-10-30 歷史與文化
孤陋寡聞,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摘下今年的諾獎桂冠之前,我從未讀過她的詩作。看到中文譯者柳向陽說:格麗克早期被稱為“後自白派”,但又超越了自白派,倒是想起了年輕時熱愛過的美國“自白派”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

(普拉斯的服裝起的是一種虛飾作用,是抵擋世界的盔甲)
1963年31歲自殺身亡的普拉斯,是少數人生與作品奇妙融合的作家。她的天賦才華,與英國詩人泰德·休斯愛恨交織的曠世之戀,至今仍是流傳的“耳語”。普拉斯傳記層出不窮,普拉斯研究生生不息,教人記起她的墓志銘:“即便在烈焰之中,也能種出金色蓮花。”
最近讀到關於普拉斯的文字,談論的是她的衣著。“她看上去就像1950年代的一個夢。”英國時尚作家特莉·紐曼在《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櫥》中寫:美國東部私校生流行的裡外兩件套,雙圈珍珠項鏈,夏季襯衣式連衣裙,這些形象幫助建造了她的神話。但就如她的散文和詩歌講述故事的方式,她的服裝起的是一種虛飾作用,是抵擋世界的盔甲,以演繹出一個更強大、更忙碌和更有用的自我。
普拉斯去世前幾年結識的女詩人露絲·芬萊特在2013年回憶:“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燃燒著勃勃雄心和智慧才華的年輕女人,試圖偽裝成恪守常規、忠誠奉獻的妻子。她戴一頂小帽,身穿寬下擺、閃閃發光的緊身墨綠色連衣裙——好似我在紐約的一個姑媽,穿成要去參加雞尾酒會的樣子。”
普拉斯為何偽裝?她的制服式、常規式著裝,是不讓自己崩潰的角色扮演。她1961年8月完成的唯一長篇小說《鐘形罩》,以維多利亞·盧卡斯的筆名發表,其實是一個自傳體故事。躲在女主角埃絲特身後,小說有一部分重新講述了1953年普拉斯在紐約《小姐》雜志工作的情形。離開曼哈頓時,埃絲特對那段膚淺生活大失所望,她扔掉了自己所有的漂亮衣裳——這正是普拉斯離開紐約返回家鄉時所為:
我抓住自己抱著的那捆衣服,拽著蒼白的一頭往外抽。一條無肩帶的松緊長襯裙落到我手中,這襯裙已經穿得沒有彈性了。我揮舞著它,像揮舞一面休戰旗,一次,兩次……微風擒住了它,我松開手。
一小片白色飄入空中,開始慢慢下降,我不知道它會歇息到哪條街或哪片屋頂……
一件又一件,我把我的衣服全部送入夜風,那些灰色的碎片震顫著,仿佛心愛之人的骨灰,它們飄走了,在紐約漆黑的心臟,散落在這裡、那裡,確切是哪裡,我永遠不會知道。
普拉斯和衣裝的複雜關係是個特例。所謂“捕捉文學與時尚交匯的驚喜瞬間”,《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櫥》逐一打開50位知名男女作家的神秘衣櫥,在多數作家那裡,衣裝是意識和思想的延伸和外化,也是有效的文學技法。喬治·桑、格特魯德·斯泰因、伊迪絲·華頓、西蒙娜·德·波伏娃、帕蒂·史密斯、蘇珊·桑塔格、托妮·莫里森、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扎迪·史密斯……眾多女作家裡,我比較喜歡的還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理念和風尚。

(伍爾夫代表了布盧姆斯伯里派的形象——無拘無束的高雅)
雖然在1927年剪過短發,經典的伍爾夫形象,是在頸項後松松綰一個發髻。“她的身材高挑,長得像只鳥”,有一雙沉思的眼睛。裹住雙肩的長款開衫成了標志,“她代表了布盧姆斯伯里派的形象——無拘無束的高雅,它已成為若無其事,不過分修飾和優雅著裝的同義詞。”把毛衣與花園勞作時穿的裙子、印花家居服和皮草坎肩、扣襻鞋和披肩混搭,這種奇特的組合比Prada的“極客時尚”早了70多年。她具有個人特質的聰慧著裝,契合度堪稱完美。
最近正讀伍爾夫1925年出版的長篇意識流小說《達洛維夫人》。故事發生在一天時間裡,達洛維夫人的生活和飽受炮彈休克症折磨的一戰老兵賽普蒂莫斯·史密斯的生活,交錯編織。伍爾夫刻意以一條綠裙子為媒介,象征歲月裡的某些時刻,經歷中的某些層次。達洛維太太縫補著她最喜愛的綠裙子,漸漸被往事淹沒,那些定義了她和她目前狀況的時刻重現在眼前。
伍爾夫說,衣服能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能改變世界對我們的看法。1920年代她曾為英國版《時尚》撰文,主編多蘿西·托德請攝影師為她拍攝一組照片,伍爾夫穿的是她母親維多利亞時代的連衣裙。典型的伍爾夫風格,既是思想上又是著裝上的一種表達。“那連衣裙不太合身,而且絕對過時——不顧時尚,毫不掩飾地懷念逝去的時光,使人憶起昔日的榮光。”
個人住在個人的衣服裡。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袖珍戲劇——你想到哪位華人女作家了嗎?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