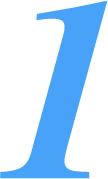海島上的家園
時間:2020-11-18 歷史與文化
一
八年過去了,我重新回到馬布島。這期間發生過許多事,讓我同島上順子一家徹底失聯。
最先是我把島上的電話號碼意外丟失了。當初辭別他們的時候,也忘了留下她家通信地址,不知怎樣才能重新聯絡上對方。
想當初,我原本是為了尋訪電影《望鄉》中阿崎婆的足跡踏上婆羅洲的,沒想到在仙本那外海這處偏僻的荒島上,遇見了當時那位離群索居的日本女大學生,了解到她在島上一段驚世駭俗的身世和經歷,將我帶入一個迷離而神奇的世界。多年過去,順子不顧世俗傳統,從日本奈良毅然來到南洋海島,義無反顧嫁給島上土著巴夭難民,幾十年如一日相夫教子的傳奇故事一直縈繞在我心上,經年難忘。
生活在仙本那岸外的巴夭人,實際上是一群國際難民。他們中很多人從菲律賓南部島嶼逃難過來,在這一帶荒島上生兒育女定居下來,卻又得不到馬來西亞的合法身份,因而只能在海上搭建難民屋,或世代生活在小船上,常被人稱作“海上遊牧民族”。
正當我想重返仙本那回訪順子一家的時候,馬布島和附近海域接二連三傳來蘇祿人綁架外國人質事件,局勢陡然惡化,令人望而卻步。
經過一系列驚險事變,馬布島上順子一家的命運究竟怎樣,他們在島上的日子是否依舊那樣安穩?經歷這些年風吹雨打,順子同她的巴夭人丈夫還會像過去一樣和諧恩愛嗎?現實生活中,他們家有沒有遭遇大的不幸和災難?島上的三個女兒都已長大成人,她們在怎樣過日子?順子父母現在還同過去一樣從奈良來島上看他們嗎?順子有沒有實現當初的願望,帶領全家回去日本?
太多的牽掛,太多的好奇,太多的懸念。我決定重返馬布島,追訪島上的順子一家。
真沒料到,現在的仙本那反而比過去更繁榮熱鬧了。
海邊那家華人開的龍門客棧依舊還在,對面海灘一帶又多了幾家度假村,規模看來都不小。小販們一路纏著觀光客,爭相推銷他們手中的鮮蝦、活蟹和海魚。遊艇發出轟轟的馬達聲,帶著一船身穿紅色救身衣的遊客在放浪的嬉笑聲中向海上進發。海面近處,小艇牽引的五色降落傘三三兩兩飛升起來,好像藍天上飄過來一串串彩色的蘑菇。
“不好意思,先生,能幫拍一張照片嗎?”我正站在海邊欣賞這一切,忽然背後傳來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帶著嬌柔的江南韻味。
我轉過身去,原來面前立著一對穿著時髦的母女,女人30出頭,小孩約莫五歲上下,一身清涼打扮。女人見我胸前掛單反相機,於是信任我,笑盈盈地把手機遞過來,讓我為她倆拍海濱合照。
女人戴墨鏡,高挑身材,長髮齊腰,穿緊身黑紗長袖高領衫,下面一襲玫瑰紅寬擺印花長裙,趿朱砂紅沙灘輕便涼鞋,戴淺色飾花垂邊草帽,讓人不禁想起電影《面紗》裡的英國吉蒂姑娘。女孩穿粉紅長袖童衫,配黑色絲質長褲,太陽鏡架上配有紅色心型花飾,鏡頭中只見一張紅撲撲稚嫩的小臉。
拍完照,我把手機送還女人手中,隨意問了問:“你們從中國哪裡來?”
“溫州。上午剛到。”她顯然有些興奮,臉上依舊掛著剛才的笑。
“就你母女倆?”
“嗯。大哥你從哪兒來?”
“新加坡。剛剛在客棧訂了兩點半的船票,等會兒去馬布島。”
“哇,這麼巧!我們也買了這班船票。”女人高興起來:“這下我們一路有伴了!”
我們就這樣臨時結伴,不久便一起登上快艇出海,向馬布島出發了。
船上包括我們,總共10來個人,左右兩邊坐得滿滿的,聽口音大多是來自中國的觀光客。青年女子叫莎莎(說是自己的網名,這樣叫方便),路上折騰一整天,此時坐在船上顯得有些困頓。小姑娘開始還興致勃勃看大海,用手嬉戲船邊飛濺起來的浪花,告訴媽媽,看見水裡好多好多的魚,還有紅色的、黃色的海星,不一會兒也就慢慢靜下來,頭靠著媽媽睡著了。
我問莎莎為什麼會來仙本那。“觀光嘍!都說這邊海上很美,又是潛水的好地方,海鮮也有名。去年我們去了馬爾代夫,今年趁國內五一長假,帶孩子來這裡玩一玩。”她說:“下次去你們新加坡!聽說那裡有個聖淘沙,島上有個環球影城,大姐一定很喜歡。”
“哪位大姐?”
她側過臉去,指指靠在自己身上熟睡的女兒,俏皮地說:“我們家裡是反串的,她叫我小姐,我叫她大姐,嘿嘿嘿嘿。”
大約一小時之後,快艇直接把我們送達馬布島上的客棧平台。
這海上客棧是旅行社新建的,除每天包吃包住外,還包船去西巴丹島潛水中心。我們各自領了客房鑰匙,回到自己的房間把行李放下,稍事休息。
窗外,陽光火辣辣地直射著,讓人難以睜開眼睛。我沖完涼,本想小憩一會兒,終因心中有事,輾轉反側睡不著。於是乾脆翻身起來,背上攝影包,獨自匆匆走出客棧,迫不及待去找尋順子的家。
二
回到巴夭人聚居的群落,一切都似曾相識,身臨其境卻又一時不辨了方向。
過去這裡好像沒有圍牆,現在卻用舊鋅鐵皮建起一道柵欄,把島上居民雞籠鴨寮一樣的屋子圍了起來。按規定,巴夭人平時不得擅自進入島上度假村,傍晚六點前必須全部回到牆內自家屋子,門口也駐有專人站崗。
我徑直來到一間巴夭人開的小賣鋪,掏出手機把八年前為順子母女拍的照片遞給對方查詢。店主拿過手機認真看了看,會意地笑了:“哦,原來你說的是那家,日本女人。沒錯,繞前面這條路一直走到頭,過去就看見了。”

(馬布島海灘上的巴夭人孩童。背景木屋即順子家面海一側後門)
順子家在圍牆外面,出去還要走一段沙灘路,遠遠見到一棵海杏樹,那就是她家了。
海杏樹是一種熱帶植物,大多生長在海邊,樹葉呈長橢圓,大而厚實。表面看上去,這種樹生長在乾燥的沙灘地上,白天經受烈日暴曬,但因樹根扎得深,反而水分飽滿,枝肥葉茂。其樹葉顏色更隨季候變化,由最先的嫩綠、橄欖綠,漸次轉為黃色、橘黃,再由紅色變為棕色、金色,最後片片脫落下來,在樹幹周圍鋪滿一地金黃。
順子的木屋建在沙灘盡頭,屋前接出一個用石棉瓦槽板蓋的棚子,裡面展賣貝殼、海螺和珊瑚礁。前面掛半截塑膠布遮陽,一側用舊鐵皮圍起來。旁邊停靠一隻銹蝕的小木船,左右兩邊橫挑一對白色的浮罐,看來已經好久沒下水了。門前沙地上豎立一根椰樹樹幹,一頭綁住巴夭人聚居區延伸過來的黑管電線,一頭用白色導線接進屋裡。
原來匍伏吊腳樓下的黃狗不見了,那群在母雞領引下嘰嘰喳喳四下覓食的雞仔也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隻白胸黑背的肥貓蹲在屋前,像當年那只黃狗一樣,睜大兩隻明晃晃的眼睛,警惕地打量著我這個不速之客。
我徑直走進棚子,提高嗓門朝屋裡喊了聲:“有人嗎?”
話音剛落,但見罩了方格鐵絲網的窗台裡閃出一個姑娘的頭來,好像似熟非熟的樣子,眨著一雙機靈的眼睛看著我。我想時隔好幾年,她一定記不得我了,於是上前把手機裡的照片給她看。
“請問,你是紀子吧?”
姑娘看了照片,沒顧得上回答我,臉上即刻露出笑容,興奮地轉過身去,高聲喊起來:“紀子!紀子!”
原來,紀子就躺在她身邊的躺椅上。她撐起身來,穿一件白色T恤,看上去比少年時略顯胖了些,但基本模樣並沒太大改變。
她把照片看了,抬起頭來又把我看了看,然後點點頭,羞澀地笑了:“想起了。記得,還記得!”
紀子現在22歲,已經長成大姑娘了。她笑起來,臉上的兩個酒窩依舊還在,而言語間卻明顯多了一份姑娘的矜持。我說,剛才差點將前面那位姑娘誤認為她了。
“那是我妹妹,久美子。”
“哦,久美子!倒是第一次見到她。欸,她人呢?”
“跑了。她在水上棧道那頭度假村打工。”
“媽媽在家嗎?”我輕輕問。
紀子點點頭,微微一笑:“在睡覺。”說過之後,依舊笑眯眯地望著我,卻並沒有回過頭去立刻喚醒媽媽的意思。
“不要緊,別打擾她,醒來以後再叫她。”我客氣地說。
“爸爸呢?”
“他在仙本那做工,明天會回來。”
我還記得上次紀子說,很想隨媽媽一起回日本看看。但那時她和兩個妹妹還小,沒資格申請護照。直到今天,當局也沒有為她們頒發護照。不過,由於母親是日本人,按日本國籍法,子女年滿18歲後可自由選擇國籍,結果三姊妹紀子、裕子和久美子拿了日本護照,在土生土長的南洋荒島上成了日本新公民。
“爸爸到今天還是申請不到馬來西亞護照,也得不到日本護照,他還是無國籍海上難民。我們一家五口,不可能拋下他一個人留在島上,所以我們至今還沒去日本。”
也許是我們的談話聲把順子吵醒了吧。我聽到裡屋傳出一點聲響,然後從裡窗見她將蚊罩慢慢卷起來扎好,悉悉索索從裡間走了出來。
三
順子依舊戴著當年那副褐色樹脂架眼鏡,穿灰色無領汗衫,一眼看上去還認得出原來的模樣,只是額前的頭髮開始有些花白,眼角也看得出歲月的蝕痕了。
她走來外間懵然見到我,一時之間回不過神來。待看過我遞去的照片後,忽然間恍然大悟。她不停用手拍打自己的腦袋,笑呵呵地說:“是啊,是啊!想起來了。哈哈,那年您從新加坡來為我們拍的。”
她一邊把手機還給我,一邊喃喃念叨:“嘿,老了,老了。”隨即走來門邊,像八年前一樣雙膝跪下,兩手搭在膝頭,同我聊起來。紀子害羞,便趁機悄悄脫身轉回裡屋去了。
順子家的基本格局和陳設大致沒有改變,上次見到的舊冰箱依舊放在同一個角落,旁邊多出一個冰廚有些顯眼。地板上鋪的白色方格地膠幾乎破損完了,現出一截一截拼合的木板,縫隙間能見到樓下的海沙。內窗牆上除掛有一本揭起的日曆,還有兩個仿真的GUCCI女式肩包,窗下木架上擺滿七七八八雜物,回收的飲料瓶罐、舊紙箱、塑膠袋,檯面上散放著幾本筆記本,幾隻圓珠筆,一本字典,還有美國當代作家斯蒂芬·金厚厚的英文小說《Under the Dome》(《穹頂之下》)。
木屋臨窗那面放了一張坐椅,一架躺椅,床墊十分破舊,用土黃色寬膠帶橫七豎八纏上若干圈,靠背上一個廢棄的汽車合成革座墊。估計剛才紀子和妹妹就躺在這裡,窗外如有人來,起身就能看到。
順子說,前兩年島上遭過一次颶風,掀起的海浪把房基下的沙土吹走大半,地基陡然低下去兩米深,於是臨時搭建了這處棚子。好在後來海沙又重新慢慢堆積起現在這樣子。
“您走後那幾年,島上鬧了好幾起綁架人質事件,那段時間真的很恐怖,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有一段時間,日本同馬來西亞兩國關係緊張,兩邊一吵架,領事館就打電話來家裡,勸我回日本。可是我怎麼可能一人回去呢?孩子們在島上,丈夫在島上。我說我不走,死也要死在一起。您說對嗎?”
我說:“紀子不是說她和兩個妹妹拿到日本護照了嗎?”
“是,可這是最近兩年才有的事。我丈夫至今還是連個合法身份都沒有,哪兒也去不了。”
她說,好在這幾年情況開始好轉了,島上也比過去更安全,而且又多建了幾家新的度假村。島上也經過培訓,要大家學會主動清除水中垃圾,而且環境保護的意識也增強了。不過現在遊客並沒有增多,過去來島上遊覽的差不多是歐洲人和日本人,現在九成以上是中國人。
順子的丈夫在為島上一家中國人開的度假村打工,度假村辦公室在仙本那鎮上,他負責每天開船運送生活物資往返島上,每週工作五天,週六周日才能回家。順子則照舊每天去海邊撿貝殼珊瑚礁,回家打掃乾淨在店中售賣。夫妻倆始終相敬如賓,相互愛慕,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改變。
“我覺得這些年我們還過得不錯,很幸福,我對我們這個家很滿意。我從來沒有改變過當初的決定,從來沒有後悔過,從來沒有。”
三個女兒中,只有老二裕子和小女兒久美子在鎮上念過高中,那時沒有身份證,也不能報考大學,只好回到家裡待著。現在裕子在鎮上一家旅遊公司當導遊,能講英語,還會華語、馬來語,懂好幾國語言。她平時住鎮上,常帶團上島來。久美子在住家背後的度假村找了份工,每天下班後回到家來,只有紀子每天陪在媽媽身邊協助打點小店生意,平日也幫助煮飯洗衣,很能幹,是家裡的好幫手。
“紀子現在22歲,有男朋友了嗎?”我忽然想起問。
順子遲疑一下,把眼光慢慢收攏來,笑了笑:“應該還沒有吧,她說自己不要結婚。”說完,又自顧自搖搖頭笑了。
“她未來的理想要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這您得問她本人嘍!”順子把頭抬起來,用手扶了扶鏡架,笑著說。
“老實說,我們作父母的始終認為,如果孩子們將來要婚嫁,最重要的是要選對人。”順子收起臉上的笑容,認認真真地說:“可現在的問題是,島上這些男孩子很多都吸毒,也沒讀過什麼書,沒有專業技能和知識,上哪兒去選好人?”
“有沒有想過走出島外,回日本或別的地方為她們物色男朋友?”
“哈哈,不可能,不可能。”順子又靦腆地笑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也希望不要嫁得太遠了,哈哈哈。”
四
“大哥,半天不見,一個人跑哪兒去了?”
我一回到客棧露天平台,就見莎莎提著網兜站在餐廳門口,笑呵呵沖著我喊。“我買了幾隻大螃蟹,讓廚房幫忙蒸好,晚上一起喝啤酒。好嗎?”
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請,並問為何不見了“大姐”。
“她今天跑累了,島上見什麼都新鮮刺激,興奮得不得了。現在在房間睡得正香呢!”
莎莎把螃蟹送進廚房出來,順手從餐桌邊拉過兩把木椅來,一把遞給我,一把她坐了。
我接過椅子,在她身邊坐下來。
大海一望無邊,夕陽在天邊漸漸西墜,雲像火一樣在天上燃燒,晚霞倒映在海面上,簇擁著舢舨歸航的剪影,一起在水中蕩漾。出海潛水的人從遠方歸來,快艇在金燦燦的水面上劃出一道道魚尾波紋,由遠而近漸漸拍打到平台基柱上,發出有節奏的喘息聲。回望島上巴夭人群落,一家家的炊煙已娉娉婷婷升起來了。
莎莎膚色白淨,生就一對丹鳳眼,配上青蔥一樣小巧玲瓏的鼻樑,鼻尖揚起,抹了唇膏,上唇微微上翹,隱隱露出一排晶瑩的白牙。海風把她一頭濃密的長髮吹得飄散開來,她不得不反復舉起手來一遍遍把它們梳攏起來。
“我和女兒都喜歡大海,每年我都會帶她出來走走看看。去年我們在馬爾代夫,前年我們跑得更遠,去了非洲的毛里求斯,那邊的海上瀉湖同這裡一樣也很漂亮,哈哈,簡直跟電影裡一樣。”
我和莎莎畢竟只是初次相識,當然不便打破砂鍋問到底,為何每次總是由她一個女人家帶孩子出國雲遊。
還在來的路上我便注意到,雖說莎莎性格開朗又健談,但她似乎從沒提及過孩子父親的事,孩子也自始至終沒有說起爸爸。這當然在我們的交談中顯得有些彆扭和不自然。不過回頭想想,或許現代都市生活中,像莎莎母女這樣的家庭組合已經成了一種“新常態”,因而也就不聞不問見怪不怪了。
“我們今天去的地方也有一大片開闊的瀉湖,水上一道長長的柚木棧道把兩個新的度假村連接起來。”莎莎自顧自繼續說。“站在棧道往下看,海水跟游泳池一樣晶瑩透亮。許多色彩斑斕的熱帶魚、海星,水中看起來一蕩一蕩的,太美了!”

她說,她們還發現一處別致的海上露天教堂,整個建築通體白色,在藍天碧海襯托下更顯得那麼聖潔典雅。據說舉辦活動時,台下兩排坐椅能容納上百人。四周柱頭上立有造型各異的海鳥木雕,“大姐”不懂海鳥的名字,只管將那裡叫“天使教堂”。她讀過安徒生童話,想像中的天使就是這樣的。
“我們本來要請你幫忙拍照,結果到處找不見人。”莎莎忽然想起來,回頭問:“對了,大哥,你怎麼一個人來旅遊?”
“我來拜會一位朋友。”
“怎麼,大哥在島上還有認識的朋友?”
“嗯,一位日本女大學生。”我平靜地說。“她嫁給了這裡的土著巴夭人。”
“嫁給島上巴夭人?”莎莎一臉迷惑,顯然一時回不過神來。
“是啊,一開始我也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卻慢慢發現,其實這日本女人活得挺自在,也挺滿足的,她覺得島上的生活很幸福。”
莎莎一邊聽,一邊不住地搖頭:“天方夜譚,真是天方夜譚!”
於是,我把順子和她一家的故事從頭到尾詳盡講給她聽了。
最後我說,人各有志,當年美國作家梭羅不也主動放棄現代都市生活,自甘到荒僻靜寂的瓦爾登湖畔獨自種地建屋自食其力去了嗎?也許在別人看來,這樣離群索居的簡樸生活不失偏激古怪,但在梭羅本人看來,這一切再正常不過了。
同梭羅比起來,順子在島上的生活當然算得上富足了。而且她並不孤單,她還有三個女兒陪伴,丈夫也始終如一愛著她。順子明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金錢是重要的。但她說,這世界上無論走去哪裡,愛情都是無法用金錢買來的。
聽到這裡,莎莎下意識地癟了癟嘴,看不出她心頭到底是理解了還是更加不理解。她想起剛才同女兒從“天使教堂”回來,曾經過一段巴夭人聚居的地方,那樣的簡陋破敗、貧瘠又骯髒。她絕對相信,那是天使永遠飛不去的地方,連上帝都把他們拋棄了。
“順子跟巴夭人住在那樣的環境裡,居然過了幾十年,她真不覺得這樣的日子過得太無望,太無聊嗎?”
“她並不羡慕都市人的生活。在她看來,許多都市里的人,包括她自家遠在奈良的妹妹,其實多數時候都過著一種病態和壓抑的生活。”
“大哥,聽你這麼說,我倒真想親眼見識見識順子的巴夭人老公到底長什麼樣,居然有這麼大的魅力,能把這日本女人的心拴在島上,而且拴得這麼緊,這麼牢!”
五
第二天,莎莎原本計畫帶女兒去西巴丹島浮潛,卻臨時改變主意,堅持要跟我一道去拜會這位傳奇的日本女人。
清晨,一彎新月從天上漸漸淡去,海面上泛起瑟瑟霞光,島上空氣清新,鳥兒在林間啁啾歌唱。一對年輕人觀賞海上日出後不舍離開,相依相偎在廊橋通道上,赤腳半懸空中,享受海風習習的愛撫。
太陽慢慢升上椰林樹梢。在去順子家的路上,我抓住時機順便拍攝幾張海景風光照,而莎莎母女自然成了我鏡頭中的模特兒。正當我們走近順子家後門不遠處,恰好見順子和紀子端一盆衣物從木屋出來清洗,與我們打個照面。
順子見我帶來兩位客人,滿臉堆笑。“我還以為您這次也是一個人上島來。”她望著我,眼中含著笑。
我向她們介紹了莎莎母女。“我們昨天來的路上才認識的。莎莎聽過你的故事,一定要來你店裡看一看。”
順子禮貌地朝莎莎鞠了一躬:“請多多關照!”隨即踩入水中,一邊同我們聊天,一邊彎身淘洗衣服。紀子有些靦腆,她朝我們堆了堆笑,趕緊返身回到屋裡去了。我和莎莎趁勢坐在沙岸上,一邊看“大姐”撿拾貝殼,一邊同順子聊起來。
“聽大哥講你們家的故事好感人,所以今天我們特來拜訪你。剛才那位是紀子吧?好清純可愛的姑娘!”莎莎說。
“嗯,是,是紀子。”順子微微一笑,對莎莎說,紀子和她最小的妹妹久美子都愛美,兩個平時在家也會上網比照人家擦脂抹粉打扮自己,尤其是久美子,會在人前害羞,但也最懂得打扮自己,還會用手機拍照放去臉書上。
“只有裕子例外,我們家老二從小不愛打扮,不描眉抹粉,她留短髮,穿牛仔褲,從不穿裙子,也不用化妝品,像個男孩子。唉,真讓人搞不懂。”
“是啊,現在的年輕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莎莎說。“對了,聽大哥講,你父母一開始也是不同意你們的婚姻,是吧?如果有一天,孩子們在婚姻愛情方面走上一條跟你們不一樣的路,你會接受嗎?”
看得出來,順子此時多少有些尷尬。她勉為其難地笑了笑,放低聲音說:“我自己?呵呵,勉強還可以吧。”她說自己也知道,無論接受還是不接受,這是孩子們的生活,需要她們自己做主。
“我也會把自己的人生經驗講給她們聽,希望她們能選擇正確的生活方式,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我從不跟孩子爭吵,跟她們的關係也比較親近,對她們抱持一種開放的態度,我尊重她們的人生選擇。不過,她爸爸可不這樣想了。”
“裕子有文身嗎?”我忽然插嘴問。巴夭人老老少少普遍熱衷文身,像達雅克人一樣。
“呵呵,她哪敢!”順子眼鋒一頓,脖子一揚,笑聲中帶有一絲冷峻:“要那樣,她爸爸不揍她才怪。”
順子清洗完衣物,重新直起身子,端起裝滿衣物的盆子踏出水來,領我們向木屋走去。
她邊走邊說,丈夫是個很強勢的人,總想控制孩子的抉擇,總會要求她們朝自己認為正確的路子走。他是穆斯林,認為女孩家就應該像女孩子,工作之餘,沒事就該呆在家裡讀書學習做家務,女孩子要溫文爾雅,不要成天在外風風火火的。
“我是沒有為此同裕子爭吵過,她爸爸就常常與她發生口角。”
我們走到木屋前,順子從裡屋搬來一方矮凳執意讓莎莎坐,自己雙膝跪在門前,兩手護膝與我們對坐交談。“大姐”站在旁邊,只顧喋喋不休向媽媽炫耀自己剛才在海灘上的戰利品。
順子父母過去每年都會從奈良來島上看望他們一家,如今年事已高,加上父親近年患上輕微老年癡呆,平時由妹妹的兒女在家照顧,所以近來也不能來島上了。不過,順子時不時還會收到媽媽寫來的信。媽媽最近也學會了用電腦,開始用Email同她聯絡,母女倆常在網絡上互傳照片,縱然遠隔萬里,親人如在眼前。
“自島上有了無線網絡,聯絡更方便了。不過,我還沒學會Skype,還不會視頻通話。不過現在這樣已經很好了。”
順子奈良家裡沒有兄弟,只有一個親妹妹。然而20多年過去,妹妹至今依舊不能理解她,不能原諒她。她怨恨姐姐下嫁巴夭人讓家人蒙羞,為此一次也不來島上看她。作為一個現代都市社會的白領職業女性,她不能認同姐姐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取向,而順子也不羡慕妹妹的生存方式,她倆各有自己鮮明不同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聽大哥講,你和丈夫在島上不怨不悔共同生活了20多年,在我們看來真是太難得了。能不能給我們講講你的丈夫,究竟他是怎樣一個人?” 莎莎一邊用手安撫女兒靜下來,一邊陪著笑,紅著臉問。
順子低下頭去,稍稍整理一下思路,然後抬起頭來對莎莎說:
“他是一個對家庭負責任的人。他沒受過什麼教育,小學三年級後就因家庭貧窮失學了。他不會英文,勉強能說一點,也能聽懂。他誠實,能吃苦,工作很賣力。”
她丈夫叫羅迪。順子講,羅迪出生在菲律賓南部蘇祿群島一個貧困的穆斯林家庭,很早父母就離異了,之後他跟母親過活。那時家貧,為幫助母親養家糊口,他從小幹過各種各樣的活計,賣塑膠袋,洗衣做飯。10多歲去船上幫人打工,20歲左右同母親一起來仙本那謀生(順子說,早年蘇祿群島同仙本那可以自由往來,沒有邊防檢查,不存在合不合法的問題,也不需要護照簽證之類的)。後來母親改嫁,生了兩個女兒留在鎮上,現在已各自成家,時不時會上島來看他們,母親卻已過世多年了。
正聊著,紀子不知從哪裡忽然冒出來,沖媽媽喊了一聲,順子立馬站起身來說聲“對不起”,即丟下我和莎莎母女,拉起牆角邊的小推車,跟在紀子身後急急匆匆向海灘跑去。
我想,一定是她丈夫從仙本那回來了。
六
果然是羅迪從鎮上回來了。
遠遠望去,羅迪生就一副結實身材,古銅膚色,穿墨綠T恤,灰色短褲,推著裝滿冰磚的推車快步往家中走來。順子跟在身後一路小跑,手搭在其中一隻扶手上,胸前的汗衫已經濕透。
羅迪比順子高出一頭,陽光把頭上的汗珠照得晶瑩發亮。順子曾在昨天電話中向他說起我,所以我們一見如故。他把車穩穩架靠在門前沙地上,含笑著走來與我們握手。順子趕緊從屋裡遞來一塊毛巾讓他擦汗,自己則回頭同紀子一起把車上的冰磚輪番抱回家,一個個放進窗台邊冰廚裡。

(日本女人順子(中)和她的巴夭人丈夫羅迪(右)。左為大女兒紀子)
這是我第一次在島上見到順子丈夫。他留小平頭,濃眉大眼,鼻樑挺直,牙齒整齊白淨,嘴唇厚實而棱角分明。他走來門前坐下,額上仍在冒汗,棕色的皮膚油光發亮,目光堅定自信,臂膀和腿肚緊扎飽滿,透著陽剛和力量。
順子存放好冰磚後,進裡屋換件紫色T恤,出來依偎在丈夫一旁,加入我們的聊天。
莎莎抓住時機,要羅迪講講自己與順子的羅曼史。
“哈哈哈,我們哪有什麼羅曼史!”羅迪一邊慌忙應答,一邊側過身去望望順子,厚道地笑了。
他說,1997年12月,順子第一次遠離父母和家鄉,從日本來西巴丹島做潛水教練。那時他也在島上度假村做船工,每天負責運輸生活用品,兩人便因此在島上認識了。順子剛來時還不會馬來話,他呢,英語也不很靈光,日語更不懂,兩人交流只能靠比比劃劃。後來時間長了,順子慢慢學會了好多馬來語,交流起來就方便了。
“記得當年那個平安夜的晚上,霓虹燈和聖誕樹把潛水中心和度假村妝扮得漂漂亮亮,到處傳來溫馨的歌聲,人們都在闔家歡慶聖誕,迎接新年的到來。我想,順子第一次來國外過節,一定會非常想家吧。於是我就主動上前問她,為什麼要離別家人,從那麼遠的地方到這島上來?我們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慢慢聊起來,日後漸漸就拍拖上,以致後來談婚論嫁,在島上組建了我們自己的家,後來有了三個孩子。”
一陣微風吹過來,將窗台上方那串竹管做的風鈴敲得叮叮噹噹響,像一道清涼的山泉溪水從我們面前緩緩流過。
莎莎偏過頭去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長髮,回頭對羅迪和順子說,她也曾陪女兒一起去日本看櫻花,甚至到過順子的家鄉奈良。在她心裡,無論怎麼說,奈良同馬布島比起來,確實一個是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羅迪聽著,接過話茬道:“老實說,有機會我也想去日本看一看。但現在還不行,我還沒有合法身份。但我對孩子們說,如果你們要去,就和媽媽一道去,不必管我。”
“你們在島上一起生活20多年,有時會鬧鬧矛盾吵吵架嗎?”莎莎又鼓起勇氣,大膽問。
“為什麼要吵?我是一個老大粗,順子肯嫁給我,別人羡慕還羡慕不過來呢!”他說,都知道順子是日本大學生,跟他一起在島上過日子,幾十年來不論環境怎樣艱難,她什麼都不挑剔,什麼都能接受,吃什麼用什麼,從來不抱怨。
“我們之間很平和。如果她在家因什麼事生氣了,我就躲出門去。你想,她在島上除了這個家,沒有親人,沒有父母親,沒有兄弟姊妹,我就是她最親近的人。為什麼要吵呢?”
羅迪為我們講這些的時候,順子一直順從地貼在丈夫身邊,靜靜地陪著笑,不插一句嘴。
“你有時會同女兒們拌嘴嗎?”莎莎還不甘心,繼續問。
“她們呢,對我們都很孝順,不過有時也會頂撞我,但是最終還是會聽我的。她們知道我是為了她們好。”
羅迪說他今年已經55歲,他常對孩子們說,現在你們已經長大了,今後談婚論嫁,一定不能把媽媽忘了。“找對象要找像爸爸一樣實幹的人。人要誠實,要努力工作。”
他說:“這些年我在鎮子上見多了,好多人光耍嘴皮子,好吃懶做,有了錢就朝三暮四、吃喝嫖賭。我告訴孩子們,千萬別找上那樣的人。”
接著,羅迪還講了許多他在鎮子上見過的人,聽過的事。
莎莎聽了,低頭不語。
離開順子家的時候,莎莎特意為女兒買下一個大海螺,說是要帶回家去做紀念。她自己則若有所思的樣子,一路沉默寡言。
天真爛漫的“大姐”在前面,懷裡抱著大海螺,一邊蹦蹦跳跳往前走,一邊歡歡喜喜自個兒唱:
小螺號滴滴滴吹,
海鷗聽了展翅飛;
小螺號滴滴滴吹,
浪花聽了笑微微;
小螺號滴滴滴吹,
聲聲喚船快歸囉……
“我覺得順子丈夫說得好,找對象就該找他那樣的人。”莎莎忽然抬起頭來,看著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語。
“我想,我肯定做不到順子那樣,放棄現有的一切來島上生活。但我將來如要結婚,我希望來島上‘天使教堂’舉辦婚禮,並請順子和羅迪做證婚人。”說完,她自己先搖了搖頭,淺淺一笑,又低頭不語了。
莎莎明天還要帶女兒續程去西巴丹島浮潛,我則要趕早班船離島,轉程回新加坡。
“大哥,將來如真能在島上舉辦婚禮,可以邀請你來參加嗎?”
“當然!我願意。”
我們重新沉寂下來,默默走在沙灘上,身後留下長長的足印。
(作者是前資深媒體人,攝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