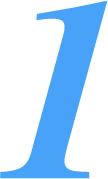一次偶遇:佩索阿與卡瓦菲斯
時間:2021-01-13 歷史與文化

紀錄片《佩索阿遇上卡瓦菲斯的那個夜晚》,虛虛實實,大膽地敘述了葡萄牙詩人、作家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和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1863-1933)在海船上的一次偶遇。
研究者在佩索阿的筆記上發現了一個名字:卡普波洛斯;又在卡瓦菲斯書寫的清單上發現了卡普波洛斯這個名字。卡普波洛斯到底是誰?學者們最後找到了卡普波洛斯的後人,並發現了他的筆記,從中得知:卡普波洛斯這位俊美的希臘退伍軍人,1929年10月在一次去美國的海輪上結識了佩索阿,又結識了卡瓦菲斯。後因在船上得知紐約股市大跌,爆發經濟危機,兩詩人下船,各自折返。由於卡普波洛斯的關係,兩位詩人在船上也遇上了,並愉快交談。90分鍾的紀錄片,如同一場夢、一部詩、一次追蹤。根據紀錄片的講述,佩索阿和卡瓦菲斯,他倆和卡普波洛斯互留了地址,有時會把自己的詩作寄給卡普波洛斯。但兩位詩人卻沒有交換地址。有一次,卡瓦菲斯寫信給卡普波洛斯要佩索阿的地址,但在收到回復前就去世了。1929年10月兩詩人在船上相遇後,此後再無交集。
查看,卡瓦菲斯年譜,1929年10月,他並無出國的記錄,可見紀錄片中的這段奇遇,是虛構的。不過,我們多麽希望“它是真的”。為什麽要虛構卡普波洛斯這個俏郎君,由他來串起兩位詩人的偶遇?耐人尋味。

(佩索阿)
佩索阿,生前及死後相當長的時間,都籍籍無名,遲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真正為世人所知。他是一位奇特的作家,有70多個筆名,準確說,不是一般意義的筆名,應該是“異名”,他設定一個異名的同時,也就設定了這個人的背景、職業、教育、個性等等,如同“創建”了一個新的自己。當他用某一個異名書寫時,他真的就附體到這個人身上。他等於有了70多個分身。讓我聯想到曹雪芹化為黛玉、寶玉、寶钗、香菱、薛蟠等人物,寫符合他們身份的詩。
佩索阿,少年時代隨母親及外交官繼父在南非生活10年,17歲回到里斯本,再沒離開。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錄》(The Book of Disquiet)1999就被著名作家韓少功譯成中文,這本書後來有了另外兩個譯本(陳實的選譯本和劉勇軍的全譯本),書名都改譯為《不安之書》。此書的影響很大,中文世界的讀者大多通過這本書認識了佩索阿。佩索阿的詩歌也出現了幾個中譯本,此外他的文論也開始有人翻譯了,一個全面的佩索阿將出現在我們面前。除了是一位詩人、散文家,佩索阿也是一個文藝批評家和哲人。
卡瓦菲斯雖是希臘詩人,但除了少年時代在英國住過七年、青年時代在君士坦丁堡住過三年,他幾乎一輩子生活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之於他,就如里斯本之於佩索阿、都柏林之於喬伊斯、布拉格之於卡夫卡,他們都是自己城市的代言人。和佩索阿一樣,卡瓦菲斯生前也名聲不顯,他基本上是一個隱士,沉溺於歷史之中。佩索阿、卡瓦菲斯和卡夫卡一樣,都是公務員,文學救贖了他們枯燥乏味的公務員生活。他們謹慎而驕傲,怯懦而孤勇。
卡瓦菲斯和佩索阿,私人情感問題有相同,也有不同。兩人都終身未婚,但佩索阿的未婚,就如卡夫卡一樣,和女友到了談論婚嫁的地步,後解除,再復合,又解除,折騰來折騰去。關於佩索阿是不是有同性戀傾向,也是一個常常被人論及的話題。肖學周《三問佩索阿》一文,就談到這個敏感問題,他說:“佩索阿顯然有同性戀傾向。他推崇的兩位大詩人莎士比亞和惠特曼都是同性戀者。佩索阿感覺自己有女性氣質,這可能是他傾向於同性戀的原因。他這樣‘詛咒’自己:‘你是個手淫者!你是個受虐狂!你是沒有男子氣概的男人!你是長著婦人心腸的男人。’如果佩索阿是同性戀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他和兩個人的關係值得注意:一個是安東尼奧·波托,一個是馬里奧·德·薩-卡內羅。”安東尼奧·波托是葡萄牙同性戀作家、唯美主義者。佩索阿開辦過一間小出版社,主要出版自己的作品,但在1922年出版了一部別人的書,它就是安東尼奧·波托的《歌謠集》,佩索阿這麽做,顯然是對安東尼奧·波托的支持、對同性戀的聲援。馬里奧·德·薩-卡內羅與佩索阿的關係,更加親密。他倆一起辦雜誌,是無話不談的密友。佩索阿曾給馬里奧·德·薩-卡內羅寫信:“我今天給你寫信,是出於情緒上的需要——向你傾訴的痛苦渴望。換句話說,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只有一句話:我今天發現自己處身於絕望的無底洞的洞底。這句荒謬的話說明了我的境況。”(《給馬里奧·德·薩-卡內羅的信》,陳實譯)信件發出一個月後,收信人馬里奧·德·薩-卡內羅就在巴黎一間小旅館裡自殺。他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是個謎。從佩索阿的信得知,他正處於“絕望的無底洞的洞底”,具有自殺的傾向,然而自殺的卻是收信人。這裡面一定存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感秘密。佩索阿寫過一首詩《安提諾烏斯》,肖學周認為:“佩索阿可能是借哈德良哀悼他的情人來影射他與薩-卡內羅的同性戀關係。”

(卡瓦菲斯)
相較於佩索阿的不確定,卡瓦菲斯是個確定的同性戀。他的詩歌感官性極強,卻又有十足的歷史感,把感官與歷史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實在找不出第二人。他的詩:敏感、憂傷、簡潔。卡瓦菲斯的詩有相當部分描寫下層社會的俊美男子,他與他們厮混於小酒館、咖啡館、戲院、廉價旅館(這些詩,一部分是他的想象並非他的親身經歷)。一朵一朵,風塵裡的花,轟然開放,旋即凋零,每一首都是時間和青春的挽歌。他在追憶錦繡繁華、似水流年。
寫到這裡,我似乎明白了——編導為什麽用虛構人物卡普波洛斯來串起兩位詩人的偶遇。卡普波洛斯不過是“美”的象征,一個替代品。又或者,卡普波洛斯不過是佩索阿創造的一個“異名”;通過他,佩索阿和卡瓦菲斯相遇。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