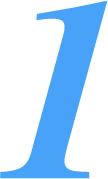動用與蔣家“私關係”是救美洲中時最後一招
時間:2019-11-04 歷史與文化
在經過幾件別人嚇自己,加上一些不無自己嚇自己成分的事情以後,余紀忠身上散發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神秘氣息。

自從9月底余先生來到紐約,就時常“神龍見首不見尾”,只有兒子余建新 (Albert) 與他形影不離。余紀忠即便在紐約,若不在報社,余建新也跟著神隱;他若離開紐約,余建新也往往隨行而去。這個情形以往並不多見。
10月18日晚上正當我準備編報的時候,難得看到了余建新出現,他神清氣爽地過來拍着我的肩膀說:“天瑞,好嗎?”我起身相迎:“坦白講,不好。”
我抓住機會向他表示,這些時候同仁們被低氣壓都壓得快喘不過氣來,總覺得報社還會發生什麼事,我也覺得好像你們在計劃着什麼。但,能不能在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以前,拜託儘量在表面上讓一切顯得如常,就像你剛才跟我打招呼那樣,免得大家的工作情緒太受影響。
余建新聽了之後拉着我到印刷廠去,那時候印刷廠還沒人上工,比較方便說話。
他把這段時間在父親余紀忠身邊感受到的內外情況,大概透露了一些,聽起來似乎余紀忠不大扛得住來自台北的壓力。
我追問,“怎麼辦?會怎麼樣?”,關報兩個字還沒出口,他又拉著我到對街經理部他辦公室去,那裡的同仁都已下班,更安靜。
余建新說:“我跟你講一件事,這是爸爸不許我講的,你絕不能對任何人講,包括曼玲嫂。”我說我是知道輕重並信守承諾的人。
於是他便告訴了我要關報的消息。同時,他還告訴了我另一個消息,那就是他將於明春返台接任《中國時報》發行人,意思是,他已排除困難,準備要當時報的接班人了。
我先恭喜了他。
但對於關報一事我即刻反應:“必須到這個地步嗎?不能先把我這個總編輯開掉,以觀後效嗎?何必關報呢?”
余建新說:“這麼做對你不公平。”
我說:“可是把報紙關了,對誰公平?”
接著我說了一些不宜關報的理由,希望余建新當作他的意見告訴他爸爸。
不過顯然余建新的重點在第二個消息上。他說,這兩件事互有關連,他能否接班要看關報的消息能否徹底保密。意思是,如果消息外漏,關不了報;關不了報,他回不了台北;回不了台北,便接不了班。他一再希望我不要害他接不了班,絕對不能對任何人透露關報的消息。
我的信守承諾成了我好大的負擔,首先使我不好主動去找余先生談,免得余建新遭父親責怪,影響了他們的父子關係,甚至影響了他的接班。於是我便只好持續找機會向他分析關報之弊。
連同這一回,在10月底之前,我們有過三次談話,前後不下10個小時。余建新約我的時候主要話題是談他接班的事,有意希望我輸誠;我約他的時候主要話題是換掉我這個總編輯,萬萬不可關報。
我反對關報,是基於多少人曾對報紙付出無數心血,以及對《美洲中時》既創價值的深刻瞭解,這不在話下。我更進一步提醒他:關報無異於打國民黨的巴掌,日後益增時報處境的困難;關報除將影響二、三百位同仁之生計,更是對《台北中時》整體士氣之重創,前途堪慮;關報是對余先生報人形象無可彌補的傷害,也是對余建新接班的“反”祝福,未來陰影難消。
這些話或許會使他心情有所觸動,不過對一個接班心切並希望好好掌握它的人來說,這樣的觸動恐怕也就那麼一會兒功夫。
我理解也尊重余建新的接班心情,在過去兩年多的共事裡,他曾多次和我聊過,幾乎一無保留。關於他們家該由哪個子女接班,曾頗令余先生傷神,老么余建新並不是“熱門股”;因事涉敏感,我從不置喙,連余先生試探性問我對他子女的看法,我都以“各有其妙”技巧性閃過。顯然,最近不知經過怎麼樣的琢磨,余建新獲得了父母的雙雙認可,他便忍不住向我透露,既難掩喜悅之情,也有爭取我這個大他五歲的“老主之臣”與他合作之意。
但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我很難將他的接班位階置於關報之上,如果他的接班必須用關閉《美洲中時》來達成,更是我完全不能認同和接受的,哪還有什麼心情輸誠?

(關報是對余先生報人形象無可彌補的傷害。作者供圖)
10月18日我在記事本上如此寫下了我當時對此事的感受:
“……似藉余先生因經濟、政治因素正感心灰意冷之時機,為求在此脱身,得以返台接事,乃做關報之積極主張。”
我因信守承諾而不能直接與余先生談,但很快就發現,與余建新談得再多,要想透過他勸阻余先生關報,完全是緣木求魚。那麼,我該怎麼做才能阻止這個決定呢?
這個決定傷害的豈是時報、時報人?它將如江南案一樣,傷害到台灣形象、國家形象,更不誇張地說,它將傷害到泛華人世界廣大而長遠的利益。
這個消息必須出去,必須要讓蔣經國知道,唯有他才能阻止發生這個悲劇,怎麼進行呢?
對於一個跑政治新聞出身的人來說,要輸送消息給黨政人士轉達於蔣,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我在文中提到過的楚崧秋、蔣孝武,甚至即使我自己直接寫信給蔣經國,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些“關係”都太“公”,我考慮必須在“私”的關係裡想出以純“私信”方式,好使此一畢竟是違反承諾的通報,顯得比較有“正當性”。
也就是,我以“私信”告之於這個人,這個人也以“私信”報之於最高當局;之後,最高當局以不落痕跡的方式“私下”將此事消弭於無形。以“最高機密”的方式在私領域裡加以破解。
誰是這麼標準的“私關係”呢?想來想去,我便想到了章孝嚴。(2005年3月,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兒子章孝嚴已改姓為蔣孝嚴)
我和孝嚴有“私關係”——他是我的表哥。他的母親章亞若女士是我父親的表妹,我的表姑。他的外婆周錦華女士是我祖父的親妹妹,我的姑婆。簡單說,三代以前,我們的祖輩是親兄妹。

(1966年,蔣家後人章孝嚴(坐者)、章孝慈在台北市青田街友人家留影)
由於孝嚴、孝慈兄弟的身份特殊,我們的這層關係是從小被叮囑不許對外說的。周錦華女士是父親在台唯一的親戚,且是父親尊敬的長輩,所以小時候便常隨父親去新竹跟這位慈祥的老人拜過年,也得見兩位長我五歲、印象中非常用功讀書的表哥。長大後,各自在不同領域工作,雖然來往不多,但婚喪喜慶必定相邀。外界少有人知道這層關係,知道的人多半得自孝嚴之口,他在自傳《蔣家門外的孩子》中也有提及。
奧運結束我回到台北,曾在離台前一天到外交部看望這位已是北美司長的表哥。他要請我吃飯卻沒了時間,便堅持來參加時報老同事次日中午與我餞別的餐會。
在大家既高興又不解他的到來時,他說:“天瑞與我有兄弟關係。”於一片驚愕中我趕忙以一句“我們有如兄弟一般”,淡化而轉移了話題。早年是不能,現在則不想讓外界知道這層關係,免得在工作上牽扯不清,孝嚴並不以為忤,微笑會意。由此可見,我們的關係何其之私。
想到便做,於是我提筆給孝嚴寫了一封長信,首先表達這是一封瞞着余家的私函,希望他永遠保守這個秘密。接着我敘述了《美洲中時》遭到的麻煩,以及余先生深陷苦惱,精神狀態相當消極,以致“有極大的可能(或者已經決定)會把在美國的報紙做個了斷。”
我在信中詳細敘述了《美洲中時》兩年來的作為,更說明並分析了這些作為的原因和效益。尤其指出,倘若《美洲中時》關門,它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海外聲望與優勢盡失,日後萬難尋回,必使親者痛、仇者快。
最後,我請他“是否可以在適當的機會和情境下,設法使當局緩和余先生的心境和處境,莫使他做下停止《美洲中時》的決定。”
這封信起筆於10月30日,考慮了好幾天,到11月6日,終於落了下款準備寄出。但是,我沒有寄!
我沒有寄是因為我的腦袋裡始終擺脫不了這些想法——
我把承諾了不對任何人說的事說出去,這是不信。
在我仍然是余先生部屬的時候,把他不欲人知的事說出去,這是不忠。
如果最終他決定不關,我如今把他沒有做的事說出去,這是不義。
最重要的是,關報是個多大的事,他總要在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意見,或起碼會告訴告訴我吧,那好像才是我合該表示意見的時候。我既會有這樣的機會,何必不信、不忠、不義呢?
想不到,我錯了!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六。
【延伸閲讀】
中時遭暗算,報人余先生要把自己送出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二)| 周天瑞
“遭逐”兩年後空降中時,難逃“被害”命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三)| 周天瑞
It is not fair!從美東喊到美西(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四)| 周天瑞
“有所為而為”,不做海外第三者(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五)| 周天瑞
觸怒僑務,一篇“檄文”引發的慘案(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六)| 周天瑞
總主筆被我“正大光明”擠走了(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八)| 周天瑞
將來遭出賣我不會意外(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九)| 周天瑞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美洲時報》便是光(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 周天瑞
《美洲中時》因奧運新聞如日中天了(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一)| 周天瑞
因言獲罪:台灣紙媒被指“掉進紅色的陷阱”(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二)| 周天瑞
一篇社論引發中美關係“海嘯”(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三)| 周天瑞
江南案的“臨門一脚”讓華文報紙走上末路(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四)| 周天瑞
“鋤奸”殺手反被鋤,“白狼”換來10年牢獄災(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五)| 周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