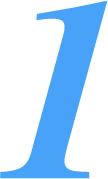寒冬來臨:海外中文媒體主編背負的紅色禁忌
時間:2019-11-21 歷史與文化
《美洲中時》停刊,又是一顆重磅炸彈,炸得海内外一片駡聲;如江南案一樣,國府再獲駡名,永遠洗刷不清。
自那日以後我們有接不完的電話,分別從台北、香港,美國各地打來,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事實,沒有人不痛駡國民黨,沒有人不希望我們快快復刊。這絕非我的個人經驗,每個時報人都感同身受,余紀忠那邊肯定更多。這個消息甚至驚動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内的美國大小媒體的關注與報導。
有人形容,這是國民黨1949年從大陸撤退之後,另一次大撤退;那一次是敗退,如今是勝退,明明贏得了人心,居然也退。也有人說,這是1970年釣魚台事件以後,台灣最失海外知識界人心之舉,預判從此紛紛左傾將成大勢,而為兩岸形勢大逆轉的分水嶺。
首先被炸醒的是國府駐外單位,在華府的駐美代表處(等同駐美大使館)發現,《美洲中時》的存在固然傷腦筋,過去幾乎就三天兩頭要拍發一些不利於它的情資回去;但當《美洲中時》停刊後才知道,原來它的功能如此之大,評價如此之高,過去聽到的雜音其實不足為訓。面對僑界四處發出的復刊呼聲,代表處見風使舵,轉而發文台北積極主張《美洲中時》復刊了。
向來七嘴八舌的僑務、黨工、情治機構也警覺到,經過《美洲中時》撤出戰場之劇變,海外文宣陣營必定此消彼長,大事不好。這些當時不遺餘力打小報告的人,此刻竟然默默推動着華人連署,呼籲政府敦促《美洲中時》重新開張。
這竟掀起了一波重視海外文宣的浪潮。而在復刊的形式上,除了希望《美洲中時》復刊以外,相關人士還盼望有財力的工商界接手,甚至還有人病急亂投醫要《中央日報》到美國開報,不一而足。這類努力起碼持續了一兩年,後來漸漸止息,終其極,榮耀難再,《美洲中時》任何形式的復刊終成泡影,再起一個如它一樣的報紙已無可能。

(圖片來源:東南大學校史文化網)
另一個面向是,余紀忠關報造成各方交相指責國府,不少人認為這是余紀忠故意給國府製造難看,有嫁禍國民黨之嫌。在國民黨眼裡,余紀忠是否只顧成全自己,犧牲黨國名聲,倒要好好解釋解釋,包括蔣經國都要找他問一問。
余紀忠在美國關報三天後回到台灣,七天後面見蔣經國,為了應付這些他一概預想得到的質疑,就改了口徑。他不敢坐實對國府的指控,沒有勇氣當着蔣經國的面,把關報當天的那番對同仁的慷慨陳詞再說一遍,於是他決心拿部下頂鍋。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他内心世界的兩面性在此時展露無遺。
天下無秘密,誰都要交差,交差的“語言”很快就傳了出來。
《美洲中時》的關報,遭到立法委員强烈的抨擊,矛頭指向政府,新聞局長張京育在答詢時當然撇清政府的責任,而他說的“語言”是“紐約編輯部與台北相隔甚遠,台北鞭長莫及,無法有效掌握,確為該報帶來困擾。”也就是表態時報關閉無關財務因素,也不再指政府刁難,而推出第三種表述:是編輯部瞎搞。
老實說,《美洲中時》結束營業,海内外聞此消息都力挺復刊,可謂“風光關報”,若非編輯部之作為深得人心,哪有這等美事?然而當面對有關當局不好交代時,上面便推稱都是編輯部惹的禍,竟自我定性《美洲中時》是“有罪”之報,並且罪在同仁。
真是成也編輯部,敗也編輯部,同一個編輯部,忽為英雄,忽為芻狗,與時俱“變”,因勢而異,令人不辨西東。
但是這一招在對付難解之局時,非常好用。明眼人都知道,關報一事本質上是對台北的一項反制行動,但只要懂得操作,亦可被解讀為“懸崖勒馬”、“認罪悔改”,那就可以既往不咎了。
余紀忠在蔣經國面前,不僅避開一切敏感字眼,以免遭疑。可想而知他必有所忠誠表白,說到痛心處不免落淚一番,於是成功地將“壯士斷腕”的憤懣轉換為“自斷一臂”的悲情。蔣經國何忍相責,能不加以慰勉嗎?各家保守單位見主子如此,還能如何?余紀忠原先經受的忠誠信任危機,豈不瞬間轉危為安,立馬迎刃而解?
縱使外有復刊之聲響徹雲霄,然而國民黨内部的大頭們,自蔣經國以降,誰有資格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地向時報傳達此意?誰又願意抱著一肚子窩囊,求他余紀忠復報?
何況面對此一呼聲,余家早已對外堅決表示不可能,第二代甚至揚言“除非余先生再生一個兒子!”凡此種種,都使國府在第一時間難以形成要求《美洲中時》復報的決策,時機一失,則復報就戛戛乎其難了。
由於余紀忠回國後相當機巧地換了說法,他過了關,這麼一來壓力便落到了我的身上。邏輯是,既然時報承認用人不當,將責任推向編輯部,身為總編輯的我,豈不正是那個所謂被用錯了的、不好駕御的人,怎麼倒還繼續在時報任職呢?
的確,余先生在告知我關報消息的同時,將我改任台北《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也就是說,他沒有讓我這個總編輯失業,授我以新的頭銜留在時報。我為免尸位素餐,還定心規劃了一個工作藍圖,打算開拓以文化藝術為內涵的紐約特派新聞生涯,從此不碰政治。
他的安排固是對老部屬的一份情誼,當然也是權宜之計,讓彼此有一個觀察和修復的緩衝段落,免得遭人批評。但很快我就聞出了異味。
關報之後,除了極少數同仁受到安排,絕大部份領了資遣費之後就流離失所,同仁情緒沸騰,對報社頗不諒解。暫時留在紐約善後的Albert便向他們散播“報紙是周天瑞搞垮的!”之說,來抵擋大家對報社的反彈情緒。這麼做,既省得傷腦筋,也正好乘機調整大家對我的觀感,可謂一石二鳥。

但同仁們自有思量,不少人聽了這一類的話很為我抱屈,即刻就會傳到我的耳朵裡。我一概默默承受了下來,心裡有數:跟時報的緣份怕是快要盡了。
沒有多久,當這個說法發展到報社必須向政府陳述時,那可就不再是個說法,而必須要拿出做法了,“處置周天瑞”是必然的結局。
果然,11月30日,Albert找我,話是這樣開始的:“天瑞啊,你在台北究竟得罪了多少人?怎麼就有人一定要你離開時報呢?”我問有些誰,他囁嚅著告訴了我三個名字,我一聽就知道是信口雌黃,因這三個政要起碼有兩個對我極好,少有人曉得。這不重要,重點在後面:“余先生希望你再回到學校去,跟幾年前一樣,報社支付學費及生活費,為時兩年。並且暫時不要回國。”這下就全明白了,不是嗎?
我是個有求去習慣的人,關報的時候就想走人,但只要我把這個心思告訴夫人曼玲,她就說,如果這麼做,當天就會開始睡不着覺。現在,我更想請辭,但下不了這個決定。
是的,身處異地,房貸、保險、教育、生活,無不需要錢,丟了工作,哪來依靠?耍帥,賭氣,秀風骨,都不能跟鈔票較勁,更不能拿家小當兒戲,畢竟我們沒有準備好啊。只好忍了下來。
在那些十分糾結的日子裡,不時會遇到陌生的讀者,但見他們手上拿着好幾份華文報,對我說,“以前只要看你們《美洲中時》,不論是新聞還是評論,就清楚了、相信了,現在卻要看這麼多!”說完還嘆一口氣。就是這樣,我走到哪裡,哪裡就為報紙隨地隨機開起“追悼會”。
相反,被《美洲中時》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世界日報》和《中報》得救了,强敵自動退兵,一切恍如天下掉下來的禮物。
《世界日報》洛杉機總經理劉自誼親口告訴我,他們被打得好慘,若我們繼續辦下去,他們連薪水都要發不出來了。《世界日報》20年後當上社長的楊仁烽對我也不諱言,當年王惕吾本已派他到紐約展開救援大計畫,力圖解決《世界日報》的困局,他知任務艱鉅,暗自發愁,哪知《美洲中時》一關,危機解除,計畫便取消了。
不同報社的人,命運真是不同。突遭大變,一群茫然失措、憤憤不平的《美洲中時》同仁,不時聚在餐館,或圍坐我家,或持着話筒,宣洩着說不完的對余先生的失望、不滿。我陪着他們同哭同笑,共度關報後的慘淡時光。
時報既說是人有問題,則造成的不只是我的受難,也不只是兩百個同仁的失業,而是他們從此由傑出人才變成戴罪之人,將被刻上印記,受到懷疑和排斥。誰來在乎他們?我曾為此私下求助於好友謝深山,央他以勞工立委的身份提出質詢,籲請政府正確看待他們,即或不能,也請不要打壓。
但迫於生計,又礙於《世界日報》通令寫明不得吸收這幫“被刻上印記的人”(該報唯獨接納了一個迫切需要的業務部經理張靜濤,因而免了楊仁烽的萬里馳援),他們只好大量去到《中報》、《北美日報》這些立場明顯相異的報紙,大大充實了異己的實力。結果又遭人指謫:看吧,果然《美洲中時》的人有問題吧,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吧。真是倒果為因,天地良心啊!
這給了我好大的警惕。常聽人說文人無行,其實文人多半缺乏財務經營的訓練和觀念,以致往往經濟上不能獨立。當經濟上不能獨立,還談什麼思想獨立、人格獨立、專業獨立、政治獨立?至於真正能堅持操守、受人尊敬的究竟有幾人?
百無聊賴之餘,我姑且一方面開始為申請入學哥大忙前忙後,一方面盤算着日後的何去何從,並等待着那最終的決定何時到來。
日曆翻過舊頁,時間前進到1985年,恩師許倬雲教授從台北回到匹兹堡家中,我們如常通了電話。在聊了很多關報心情和台北見聞後,他突然問我:

(歷史學家許倬雲,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圖片來源自網絡)
“你有沒有勸過余先生到大陸辦報?”
我問“怎麼回事?”
許老師說,他去看了余先生,一見面劈頭就問余紀忠:
“您囑託過我,要像當年沈剛伯老師在倫敦照顧您一樣,在匹茲堡照顧天瑞,我現在最關心的還是我的這個學生,您把報紙關了,打算怎麼待他?”
余告訴許老師已讓我離開工作,資助我重回學校,接着加了一句:“天瑞到了美國以後變了。”
老師問:“怎麼變了?”
余說:“他變左了。”
老師說:“我和天瑞常有聯繫,並沒這個感覺,您何以見得?”
余便像是說出一個驚天大秘密似地,告訴許老師我勸他到大陸辦報的事。
我一聽完這段敘述,當即決定辭職,這一回,曼玲沒再阻止我。
究竟怎麼回事?
我依稀想起,在籌辦報紙當時,大家同甘共苦,相互砥礪,充滿豪情壯志,和余先生之間宛如革命伙伴一般無所不談,有時不免會天馬行空地“盍各言爾志”起來。我曾說“哪怕余先生若要我去非洲辦報,我都辦給他看!”就是這個情境下的語言。
於是那句話應該是這樣說的:我們一定要把《美洲中時》辦好,將來還要在世界各地辦,說不定哪天也能在中國大陸辦,讓《中國時報》遍地開花,成為全球“時報王國”!
這是勸他去大陸辦報?
那時候兩岸還處在什麼都不通的完全封閉狀態,余先生還是國民黨中央常委。我“勸他”去大陸辦報?我瘋了嗎?
在那個大禁忌時代,“變左了”可不是句好話,說這話等於扣我紅帽子。余既會對老師說,必也會對有關方面說,不知道跟了多少人說,那不是置我於死地麼?
在報社把問題歸咎于編輯部的時候,我沒對外說一句話,也沒回台灣為自己開脱,默默承擔了下來。畢竟知遇一場,在他遭難的時候替他有所承擔也是應當。但是落井可以,落井下石不行。

事已至此,我徹底發現,這老闆不能再追隨了,既然已是“郵差三度來敲門”,可不能再遲疑了。1月22日,就在我重回學校的第一天,一封忍了很久的辭職信,終於投進了哥大校區的郵筒裡。
我謝絕了余老闆再次助我深造,同時表達了堅決的辭意,堅決到一看便知無法慰留。
我依然感謝他的提攜栽培,遺憾肇致他以壯士斷腕之決心停止新報;但也表示,“天瑞固難辭其咎,然亦恐不能獨任其罪,個中因由蓋可謂一言難盡。”
我還說,“今後行止,自會切守一貫之分際”,臨走都不忘讓他放心,我不會去到他最在意的“敵營”聯合報系。
最後祝福他“福壽無疆,大業長興”。
十三年多的賓主關係,就此劃下句點。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十八。
【延伸閲讀】
中時遭暗算,報人余先生要把自己送出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二)| 周天瑞
“遭逐”兩年後空降中時,難逃“被害”命運?(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三)| 周天瑞
It is not fair!從美東喊到美西(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四)| 周天瑞
“有所為而為”,不做海外第三者(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五)| 周天瑞
觸怒僑務,一篇“檄文”引發的慘案(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六)| 周天瑞
總主筆被我“正大光明”擠走了(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八)| 周天瑞
將來遭出賣我不會意外(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九)| 周天瑞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美洲時報》便是光(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 周天瑞
《美洲中時》因奧運新聞如日中天了(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一)| 周天瑞
因言獲罪:台灣紙媒被指“掉進紅色的陷阱”(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二)| 周天瑞
一篇社論引發中美關係“海嘯”(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三)| 周天瑞
江南案的“臨門一脚”讓華文報紙走上末路(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四)| 周天瑞
“鋤奸”殺手反被鋤,“白狼”換來10年牢獄災(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五)| 周天瑞
動用與蔣家“私關係”是救美洲中時最後一招(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六)| 周天瑞
报纸之死:解密“被”停刊的至暗时刻(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十七)| 周天瑞